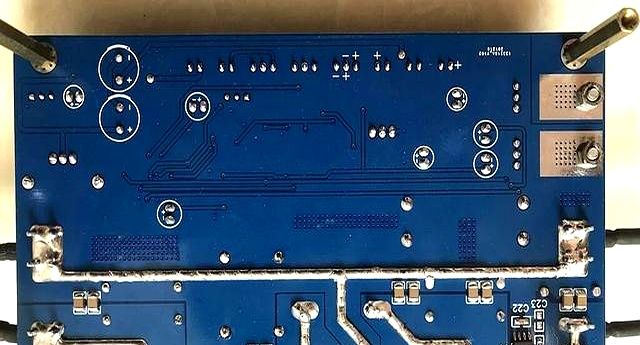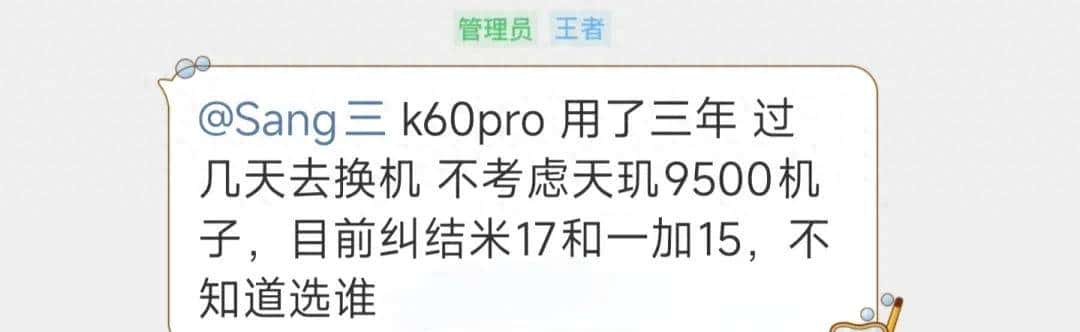林小满在废品站发现那只老式座钟时,指尖刚触到冰凉的黄铜外壳,钟摆就“咔嗒”响了一声——明明三天前暴雨冲垮了电路,整个废品站连应急灯都没亮,这钟的表盘却透出层暖黄的光,像有团揉碎的夕阳裹在玻璃里。
“这钟早该拆了卖铜。”废品站的老刘叼着烟,一脚踢在钟底座上,“上个月收的,原主是巷尾修表的老陈,走之前说这钟有‘毛病’,谁碰谁倒霉。”
林小满没听劝。她刚从美院毕业,租的小阁楼缺个像样的摆设,这钟的罗马数字刻得精致,钟面还嵌着圈细珍珠,就算坏了也能当装饰。她抱着钟往回走时,钟摆又轻轻晃了晃,怀里像揣了只刚睡醒的猫,软乎乎的动静顺着胳膊往心里钻。
回到阁楼,林小满擦了半宿钟上的灰,才发现底座内侧刻着行小字:“第七个齿轮转时,寻钟摆指向的光。”她翻遍钟表维修手册,也没见过哪款座钟有七个齿轮——普通座钟最多五个,负责走时、报时和摆幅,第七个齿轮根本不合机械原理,倒像句没头没尾的谜语。
真正怪事发生在当晚。林小满被一阵规律的“滴答”声吵醒,睁眼就看见那只座钟亮着,钟摆正以一种诡异的速度转动,不是左右晃,而是绕着表盘打圈,像在画看不见的圆。她伸手去按钟摆,指尖却穿过了暖黄的光——那光不是从表盘里透出来的,是从钟内部的齿轮间渗出来的,最里面的位置,果然有个比其他齿轮小一圈的银色齿轮,正慢慢转着,齿牙上还缠着根褪色的红绳。
“你也在找它吗?”
林小满猛地回头,门口站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辫子上系着和齿轮上一样的红绳,手里还攥着块碎掉的表蒙子。姑娘的身影半透明,脚边没有影子,说话时带着股旧木头的香气,和座钟的味道一模一样。
“你是……”林小满攥紧了被子,却没觉得害怕——姑娘的眼睛很亮,像钟面上没蒙尘的珍珠。
“我叫陈晚,这钟是我爹做的。”姑娘走到钟旁,指尖轻轻搭在玻璃上,“民国三十一年,日本人占了城,我爹是镇上唯一会修钟的,他们逼他给军用计时器上发条,他不肯,就把最重大的零件藏进了这钟里。”
林小满顺着她的手看去,第七个齿轮转得更快了,光也更亮,隐约能看见齿轮里嵌着个小金属片,上面刻着复杂的纹路。
“那是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没了它,日本人的炸弹就定不了时。”陈晚的声音低了些,“我爹把零件藏好的第二天,就被他们带走了,走之前说,等第七个齿轮转起来,让我跟着钟摆的光走,就能找到他藏的‘另一样东西’。可我等了三天,钟没动静,城却被炸了,我……”
她的身影开始变淡,像被风吹散的雾。林小满急了,伸手去抓她的袖子,却只碰到一片冰凉的空气:“你还没说,光指向哪里?”
“钟摆停的时候,看它对着的方向……”陈晚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融进了钟的“滴答”声里。座钟的光突然暗了下去,钟摆也恢复了正常的左右晃动,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梦——但底座上的小字还在,第七个齿轮也还在转。
接下来的几天,林小满总在深夜被钟吵醒,每次陈晚都会出现,说些零碎的往事:她爹教她认齿轮时,会把糖藏在钟芯里;她第一次独立修好的钟,是给隔壁老奶奶的;日本人来的前一晚,她爹把红绳系在她辫子上,说“这样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可每次问到“另一样东西”,陈晚的身影就会变淡,像是有什么力量在阻止她。
直到第七天,林小满发现钟摆的光变了颜色,从暖黄变成了淡蓝,像凌晨的天。陈晚这次没说话,只是指了指钟摆,又指了指阁楼的窗户。林小满顺着钟摆的方向看去,窗外是条老巷,巷尾正是老刘说的“老陈修表铺”,目前已经改成了水果店。
“零件藏在钟里,那‘另一样东西’,会不会在修表铺?”林小满心里一动,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水果店。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听她说起老陈,愣了愣:“你说的是陈师傅?我小时候总去他铺子里玩,他铺子里有个铁盒子,说要留给‘等钟转的人’,后来铺子拆迁,我把盒子收起来了,以为是他的旧工具。”
男人从里屋拿出个生锈的铁盒,打开的瞬间,林小满看见里面放着本泛黄的笔记本,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长衫,手里抱着个小姑娘,辫子上系着红绳,正是陈晚和她爹。笔记本里记满了修钟的技巧,最后几页却画着地图,标着“城西老槐树”“北关水井”,最末尾写着:“零件可毁,地图不可丢,待和平日,寻此标记,埋炸药之处皆可平,保乡邻平安。”
原来老陈藏的不是金银,是日本人埋炸药的位置。林小满抱着笔记本回到阁楼,座钟的光又亮了,这次陈晚的身影很清晰,手里还拿着那片碎表蒙子:“我爹说,等和平了,要把这些地方都种上花,说钟表是记时间的,可最好的时间,是不用怕炸弹的时间。”
钟摆突然停了,指着窗外的老槐树。林小满想起笔记本里的地图,老槐树下标着“一号”,她赶紧找了把铲子去了老槐树,在树根下挖了半米,果然挖出个铁皮箱,里面装着十几张图纸,都是日本人的军事部署图,还有一张陈晚的照片,背面写着:“晚晚,爹等不到你长大了,但爹护着的城,会替爹看着你。”
林小满把图纸和笔记本交给了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说,这些资料填补了抗战时期本地的史料空白,很有价值。她再回到阁楼时,座钟的第七个齿轮不转了,光也消失了,钟摆安安静静地左右晃着,像普通的座钟一样。
那天晚上,林小满没被钟吵醒,却做了个梦。梦里陈晚穿着蓝布衫,辫子上的红绳飘着,拉着她爹的手,站在开满花的巷子里,笑着说:“爹,钟转了,光也找到了,我们回家了。”
醒来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钟上,钟面的珍珠闪着光,林小满摸了摸底座的小字,突然清楚——老陈的宝藏从来不是零件和图纸,是一个父亲想护女儿、护家乡的心意,是就算隔着岁月,也能顺着光找到的,藏在齿轮里的温柔。
后来林小满把座钟留在了档案馆,和那些图纸放在一起。偶尔她去看,会看见钟摆轻轻晃一下,像在跟她打招呼,也像在告知所有人:有些故事,会跟着钟表的“滴答”声,一直走下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