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太阳毒得像个后娘,把地里的泥块都晒得冒了白烟。
我光着膀子,只穿了条洗得发白的大裤衩,猫着腰,像只没安好心的黄鼠狼,溜进了大队书记家的瓜地。
空气里全是瓜果被晒透了的甜腻味儿,混着泥土的腥气,一个劲儿地往鼻子里钻。
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喊得人心烦意乱,也喊得我心跳如鼓。
砰,砰,砰。
每一下都像砸在我自己耳朵里。
我不是天生的贼骨头。
实在是家里奶奶咳得厉害,一晚上都睡不安稳,嘴里念叨着,想吃口甜的、带水的。
那时候,村里谁家有闲钱买西瓜?
只有大队书记家,在自留地边上开了这么一小片瓜地,伺候得精贵。
瓜藤绿油油的,肥大的叶子底下,藏着一个个滚圆的青皮大西瓜,像一群懒洋洋的猪仔,趴在地上晒太阳。
我盯上最大最圆的那个,已经好几天了。
它屁股上的花纹都散开了,瓜脐也缩成了一个小黑点,藤蔓都打了蔫。
村里老人说,这瓜,熟透了。
我咽了口唾沫,唾沫是苦的,嗓子眼儿里像着了火。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高粱地的哗啦声,和那要命的蝉鸣。
我像条泥鳅,哧溜一下就钻进了瓜地。
脚踩在被晒得滚烫的泥土上,烫得我一激灵。
我顾不上这些,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瓜,匍匐前进。
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眨了眨眼,忍着,手已经摸到了那个瓜。
冰凉,光滑。
像摸到了一块玉。
我心里一阵狂喜,用手指在瓜皮上轻轻弹了一下。
“梆梆梆”的声音,清脆,沉闷。
好瓜!
我抱住它,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把瓜蒂拧断。
可那瓜蒂韧得很,像根牛筋。
我急得满头大汗,正跟那瓜蒂较劲,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
“你干啥呢?”
那声音不大,却像个炸雷,在我头顶上“轰”的一声炸开。
我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
整个人僵在原地,像被点了穴,一动不敢动。
怀里还死死抱着那个大西瓜。
完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
被抓住了。
还是被大队书记家的人抓住了。
这下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爸妈不在,就我跟奶奶相依为命,我要是出了事,奶奶可怎么办?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
身后站着个姑娘,跟我差不多大,可能还小一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的确良衬衫,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扎着。
皮肤是那种常年在田里干活的麦色,但眼睛特别亮,像水洗过的黑葡萄。
是林书记的闺女,林晚。
她手里提着个水桶,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嘲笑,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
我抱着瓜,像抱着个烫手的山芋,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尖。
热辣辣的,比头顶的太阳还烫。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想吃瓜?”她又问了一句,声音还是那么平静。
我胡乱地点了点头,又飞快地摇了摇头。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
她看着我怀里的瓜,又看了看我涨得通红的脸,嘴角忽然微微翘了一下。
“这瓜,还没完全熟透,摘了可惜。”
我一听,心里更慌了。
这是要教训我了?
我把瓜往地上一放,低着头,准备挨骂,或者挨打。
村里孩子偷东西被抓住,少不了一顿胖揍。
我把脖子一缩,等着。
可等了半天,预想中的巴掌和骂声都没来。
我偷偷抬眼皮瞅了她一眼。
她正看着远处那片被太阳烤得蔫头耷脑的玉米地,眉头微微皱着。
“地太干了。”她自言自语似的说。
然后,她把目光转回到我身上。
“瓜给你。”
我愣住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你说啥?”我傻乎乎地问。
“我说,这个瓜,可以给你。”她重复了一遍,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我脑子“嗡”的一声,彻底懵了。
这……这是什么路数?
偷东西被抓,不但不挨揍,失主还要把东西送给我?
我看着她,张着嘴,像条离了水的鱼。
她指了指不远处地头的一台手压式水泵,和一排排长长的水渠。
“你帮我浇地。”
“瓜给你,你帮我浇地。”
她说完,把手里的水桶往地上一放,看着我,等我的回答。
阳光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
我看着她,又看看那个大西瓜,再看看那片望不到头的玉米地。
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那个下午,我才知道,浇地是个多么累人的活儿。
手压式的水泵,要用全身的力气去压,才能把水从深深的井里抽上来。
压杆又重又涩,压不了几下,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
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我身上往下淌,把脚下的泥土都浸湿了一片。
林晚也没闲着。
我负责压水,她负责引导水流。
她拿着一把铁锹,在地垄沟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在这里堵个口,一会儿在那里开个豁。
水流顺着她挖开的渠道,“哗啦啦”地流进干涸的玉米地里。
泥土贪婪地吮吸着水分,发出“滋滋”的声响,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儿。
很好闻。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
只有水泵“嘎吱嘎吱”的响声,和水流的“哗啦啦”声。
太阳慢慢地往西边落,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我累得快虚脱了,感觉骨头架子都要散了。
可我一声没吭,咬着牙,一下一下地压着水泵。
这是交换。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用我的力气,换那个西瓜,也换我的尊严。
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晚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行了,今天就到这吧。”
我停下来,扶着水泵,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她走到瓜地里,把我之前看上的那个瓜摘了下来,抱到我面前。
“给。”
那个瓜沉甸甸的,我接过来,差点没抱住。
“谢谢。”我小声说,声音嘶哑。
“不客气。”她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你力气还挺大。”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她提起水桶,转身要走。
“等等。”我叫住她。
她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把瓜递过去,“你……你也吃。”
一个人吃这么大的瓜,我心里过意不去。
她摇了摇头,“你拿回去吧,给你奶奶吃。”
我心里一震。
她怎么知道?
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听村里王大娘说的,你奶奶病了。”
我的脸又红了。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她不是不知道我偷瓜,她只是……给了我一个台阶下。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西瓜,站在夕阳里,看着她纤瘦的背影消失在小路的尽头。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有羞愧,有感激,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暖的东西,在胸口慢慢化开。
那个西瓜,我抱回家,切开。
红色的瓜瓤,黑色的瓜子,像一幅画。
奶奶吃得特别开心,她说,这是她这辈子吃过最甜的瓜。
我也觉得甜。
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
从那天起,我好像就跟林晚有了某种默契。
每天下午,我都会主动去她家地里,帮她浇地。
她爹,林书记,白天要去大队部开会,地里的活儿,许多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从不叫苦。
我去了,她也不多说,只是默默地递给我一把铁锹,或者指指那个手压水泵。
我们就这样,一个压水,一个引流,默默地干活。
太阳把我们的皮肤晒得黝黑,汗水浸透了我们的衣衫。
有时候,我们会坐在田埂上休憩。
她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除了课本之外的书。
书的封面是牛皮纸的,已经有些卷边了,上面写着几个我认不全的字。
她看得很专注,手指轻轻地划过那些文字,像是抚摸着什么宝贝。
“你看的什么?”我忍不住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
我不懂。
“讲什么的?”
“讲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人,怎么跟命运斗争,把自己炼成钢铁的故事。”
她的眼睛里闪着光。
那种光,我从来没在村里其他姑娘的眼睛里看到过。
那是一种对远方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
“好看吗?”
“好看。”她点头,“人活着,不能就像地里的庄稼,春天发芽,秋天收割,就完了。得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似懂非懂。
“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她想了想,说:“就像保尔,他眼睛瞎了,身体瘫了,可他还在写作,他觉得他的生命还在燃烧。那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沉默了。
我看着她被晒得有些发红的脸颊,看着她手里那本破旧的书,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觉得,我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只想着怎么填饱肚子,怎么让奶奶过得好一点。
而她,想的是生命,是燃烧,是钢铁。
那些词,离我太遥远了。
“你也想变成钢铁吗?”我问。
她笑了,摇摇头,“我不想变成钢铁,我想去看看炼钢的炉子是什么样的。”
她指着远方,太阳落下去的地方。
“书上说,山的那边,有城市,有高楼,有大学。我想去那里看看。”
我的心,被她的话轻轻地撞了一下。
大学。
那是个更遥远的名词。
我们村,多少年才出一个高中生,大学生,那简直是传说中的人物。
“你能考上吗?”
“我不知道,但我会拼命学的。”她的语气很坚定。
那天之后,她开始给我讲书里的故事。
讲保尔,讲冬妮娅,讲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名字,从未想象过的生活。
她讲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夜空里的星星。
我听得入了迷。
我发现,原来除了村里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有时候,她会把看过的书借给我。
我如获至宝。
晚上,奶奶睡下后,我就点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趴在炕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那些书。
许多字我不认识,就圈起来,第二天去问她。
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
我的世界,像被推开了一扇窗。
窗外,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新世界。
我开始贪婪地阅读。
《红岩》、《青春之歌》、《牛虻》……一本又一本。
那些书,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道又一道的门。
我不再仅仅是那个只知道下地干活,偷瓜给奶奶吃的野小子。
我的脑子里,开始装进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和林晚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不再只是默默干活的搭档。
我们会聊许多天。
聊书里的英雄,聊未来的梦想,聊彼此的心事。
我知道了她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她跟她爸相依为命。
她也知道了,我爸妈在外地打工,一年也回不来一次。
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
在那个贫瘠而闭塞的村庄里,我们像两株依偎在一起的小树,相互取暖,相互支撑。
那年秋天,玉米丰收了。
金黄的玉米棒子,像一排排金元宝,堆在场院里。
林书记很高兴,在家里摆了酒,请了几个村干部吃饭。
我也被林晚叫去了。
林书记看到我,愣了一下。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平时在村里很有威严。
“小远来了。”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有些局促,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爹,夏天浇地,多亏了陈远帮忙。”林晚替我解围。
林书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嗯,坐吧。”
那顿饭,我吃得坐立不安。
桌上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只有我埋着头,一声不吭。
我能感觉到,林书记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在我身上。
那目光像针一样,扎得我浑身不自在。
吃完饭,我赶紧告辞。
林晚送我到门口。
月光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
“我爹他……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她说。
我摇摇头,“没事。”
我怎么会往心里去?
我一个偷瓜贼,人家没把我打出去,还让我上桌吃饭,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情了。
“林晚,”我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眼睛,“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的瓜,也谢谢你的书。”
没有那个瓜,就没有我们的相识。
没有那些书,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混小子。
她笑了,月光洒在她的睫毛上,像镀了一层银霜。
“你要真想谢我,就好好读书。”
“嗯。”我重重地点头。
“我们一起考出去,去山那边的城市,好不好?”她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我的心,在那一刻,跳得飞快。
“好。”
我听见自己说。
那个承诺,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我的心田里。
从那天起,我学习更加拼命了。
白天跟着村里的老师上课,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复习。
林晚也常常给我送来一些复习资料,那是她托城里的亲戚买的。
我们的关系,村里渐渐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我一个穷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攀林书记家的高枝。
那些话,像刀子一样,割得我心里不舒服。
我开始刻意躲着林晚。
她来找我,我也总是找借口避开。
我怕那些流言蜚语,会伤害到她。
她是个好姑娘,不应该由于我,被人指指点点。
有一天,她在我回家的路上堵住了我。
“你为什么躲着我?”她问,眼睛红红的。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没有。”
“你就有!”她声音里带了哭腔,“是不是由于村里人说的那些话?”
我沉默了。
“陈远,你看着我。”她抓住我的胳膊。
我被迫抬起头,对上她那双含着泪的眸子。
“我们说好的,要一起考出去,你忘了吗?”
“我没忘。”
“那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你怕了?”
我怕了。
我真的怕了。
我怕我配不上她。
她那么好,像天上的月亮。
而我,只是地上的泥土。
“林晚,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艰难地说出这句话。
她愣住了,抓着我胳膊的手,慢慢松开了。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一颗,一颗,砸在干燥的土地上,瞬间就没了踪影。
“陈远,你混蛋!”
她哭着跑开了。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心像被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疼得厉害。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想了许多。
想她明亮的眼睛,想她借给我的那些书,想她在田埂上跟我说过的梦想。
她说,人活着,不能就像地里的庄稼。
她说,她想去看看炼钢的炉子。
她说,我们一起考出去。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
第二天,我去找她。
她家门关着。
我敲了半天,没人开。
邻居王大娘告知我,林书记一大早就带着林晚,坐车去县城了,说是要去她舅舅家住一段时间,准备中考。
我站在她家门口,呆呆地站了很久。
心里的那点火苗,像是被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灭了。
她走了。
连声招呼都没跟我打。
她是不是,也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段时间,我像丢了魂一样。
上课没心思,干活没力气。
奶奶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怎么说?
说我喜爱上了一个我根本配不上的姑娘?
说我做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目前梦醒了?
中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我看着桌上堆得高高的复习资料,那些都是林晚给我的。
上面还有她用红笔做的标记和笔记。
字迹娟秀,清清楚楚。
我拿起一本书,摩挲着上面熟悉的字迹,眼眶一热。
不。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她说得对,我不能当个懦夫。
就算她走了,我也要兑现我的承诺。
我要考出去。
我要去山那边的城市。
我要让她看看,我陈远,不是个混蛋!
我重新把头埋进了书本里。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
饿了,就啃个凉窝头。
我把林晚给我的那些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刻进了我的脑子里。
那股狠劲,连我自己都害怕。
中考那天,天气很好。
我走进考场,心里异常平静。
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改变命运的机会。
考试结果出来的那天,我正在地里帮奶奶锄草。
村里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路喊着我的名字。
“陈远!陈远!你的通知书!”
我扔下锄头,飞奔过去。
那是一封来自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红色的纸,烫金的字。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却在不停地发抖。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我仰起头,看着蓝得耀眼的天,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奶奶也哭了。
她抱着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孙子有出息了,有出息了……”
那天,我们家像过年一样。
奶奶杀了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给我炖了汤。
那是我长那么大,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可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我考上了,林晚呢?
她考得怎么样?
她……还在县城吗?
我去她家找过几次,门一直锁着。
我向村里人打听,也没人知道她的消息。
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
开学那天,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奶奶给我准备的干粮,一个人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县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
能来这里上学的,都是各个乡镇的尖子生。
我穿着打着补丁的旧衣服,站在一群穿着光鲜的同学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我有些自卑,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
我能在这里待下去吗?
我能跟得上这里的学习进度吗?
林晚,你又在哪里?
开学典礼上,校长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
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心不在焉。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下面,我们有请新生代表,林晚同学发言!”
我猛地抬起头。
一个穿着白衬衫、蓝裙子的女生,走上了主席台。
她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身姿挺拔。
是她!
真的是她!
她瘦了,也高了,但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点都没变。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她也考上了一中!
她就站在那里,站在全校师生的面前,侃侃而谈。
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校园。
她说,她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她的梦想,是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说,她信任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她会用三年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
她的发言,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她,眼睛湿润了。
我们,又在同一个地方了。
虽然,我们之间,好像隔着千山万水。
典礼结束后,我鼓起勇气,想去找她。
可她身边,围了太多的人。
老师,同学,都争着跟她说话。
我挤不进去。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
她好像也看到了我,目光在我们这边扫过,但很快就移开了。
她……是不是不想认我了?
我心里一阵失落。
也是,我目前这个样子,又穷又土,她怎么会认我呢?
开学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高中的课程又多又难,我这个从村里来的学生,基础薄弱,学起来很吃力。
每个月的生活费,也让我捉襟见肘。
我每天只吃两个馒头,就着免费的菜汤。
晚上,等宿舍的同学都睡了,我还要偷偷跑到路灯下,多看一会儿书。
我很少跟人说话,也很少参与集体活动。
在同学眼里,我是一个孤僻、贫穷的怪人。
我和林晚,被分在了不同的班级。
她是重点班的学生,成绩优异,是老师眼中的宠儿,同学眼中的学霸。
而我,只是普通班里一个不起眼的差生。
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遇到。
她总是和一群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
我每次都只是低着头,从她身边匆匆走过。
我不敢跟她打招呼。
我怕我的出现,会给她带来困扰。
我怕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我只能把所有的思念和痛苦,都埋在心底,化作学习的动力。
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疯狂地啃着书本。
我的成绩,开始一点点地往上爬。
从班级倒数,到中游,再到前几名。
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
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了我,说我是进步最大的学生。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喜悦,只有酸楚。
我这么努力,只是想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
可是你,知道吗?
那天晚自习后,我像往常一样,去路灯下看书。
一个身影,悄悄地走到了我身边。
“陈远。”
是林晚的声音。
我浑身一僵,抬起头。
她就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给你的。”她把红薯递给我。
我没有接。
“你怎么来了?”我问,声音有些干涩。
“我听你们班主任说,你很用功。”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嗯。”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她小声问。
我摇摇头。
我从来没有生过她的气。
我只是气我自己。
“那天……我不是故意不辞而别的。”她解释道,“是我爸,他知道了我们的事,硬把我带到县城,不让我跟你联系。”
我心里一颤。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她说,“我应该想办法告知你的。”
“没事,都过去了。”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她把红薯塞到我手里。
“快吃吧,还热着。”
红薯很烫,暖意从我的手心,一直传到心里。
我剥开皮,咬了一口。
又香又甜。
“你……最近还好吗?”她问。
“挺好的。”
“学习跟得上吗?”
“嗯。”
我们之间,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陈远,”她忽然开口,“我们还是朋友,对吗?”
我看着她期待的眼神,用力地点了点头。
“是。”
她笑了,像以前一样,露出两颗小虎牙。
“那后来,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问我。”
“好。”
从那天起,我们又恢复了联系。
我们不敢在白天见面,只能在晚自习后,在校园那个僻静的角落里,偷偷地见上一面。
她会给我带一些好吃的,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个鸡蛋。
她会给我讲一些难题的解题思路。
我也会跟她聊聊我最近看的书。
那段时光,是我整个高中时代,最温暖、最明亮的记忆。
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像两只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的萤火虫,用彼此微弱的光,照亮对方的路。
我们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我们成了老师口中,最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高三那年,学习变得更加紧张。
我们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最后的冲刺中。
我们约定,要考同一所大学。
北京。
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高考前一天晚上,她来找我。
她塞给我一张纸条。
“考场上见。”
纸条上,只有这四个字。
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高考那几天,我发挥得异常出色。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都能实现梦想。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
我回到了村里,帮奶奶干农活。
我每天都会去村口,等邮递员。
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等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北京大学。
我看着那四个烫金的大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做到了!
我真的做到了!
我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知林晚。
我跑到她家。
门,还是锁着。
我向村里人打听。
他们说,林书记一家,早就搬到县城去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她考得怎么样?
她去了哪里?
我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个夏天,我是在无尽的思念和等待中度过的。
开学前,我给林晚在县城的旧地址,写了一封信。
我告知她,我考上了北大。
我问她,她考得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在北京相遇。
我把我们所有的过去,所有的约定,都写进了信里。
那封信,石沉大海。
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带着一丝失落和迷茫,我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绿皮火车,咣当咣当,载着我的青春和梦想,驶向那个陌生的城市。
北京,那么大,那么繁华。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感觉自己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我能在这里,找到她吗?
大学生活,比高中要丰富多彩得多。
但我过得依然很清苦。
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就去做各种兼职。
发传单,做家教,去餐厅洗盘子。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我不敢让自己停下来。
我怕一停下来,就会想起她。
我去了北京所有的大学,一遍一遍地翻看新生的名单。
没有。
没有林晚这个名字。
她到底去了哪里?
难道说,她没考上大学?
不可能。
以她的成绩,绝对不可能。
那她为什么不联系我?
无数个夜晚,我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
我想不通。
大二那年,我利用暑假,回了一趟老家。
村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更破败了。
我去了林晚家的老屋。
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门上的锁,已经生了锈。
我找到了当年的王大娘。
她告知我,林书记,在林晚高考后不久,就由于贪污受贿,被抓了。
这个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打懵了。
“那……那林晚呢?”我颤抖着问。
王大娘叹了口气。
“那孩子,也可怜。她爹一出事,家里就被封了。她一个人,拿着大学通知书,哭了好几天。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大学通知书?”我追问,“她考上哪儿了?”
“好像……也是北京的,叫什么……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
离我们学校,只有两站地!
我的心,狂跳起来。
原来,她也来了北京。
可是,她为什么不去找我?
“她爹出事,对她打击太大了。”王大娘说,“听说,她把通知书都撕了,说不上了。”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能想象,一个刚成年的女孩,面对那样的家庭变故,是多么的无助和绝望。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回来?
为什么我没有陪在她身边?
我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就去了人民大学。
我查了当年的新生档案。
有林晚的名字。
但是,报到状态是:未报到。
她真的,放弃了。
我像疯了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她。
我去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
火车站,汽车站,人才市场……
没有。
哪里都没有她的身影。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即将毕业的社会人。
我成绩优异,拿到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我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了导师最得意的门生。
我变得越来越优秀。
可是,我却越来越不快乐。
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空洞。
那个空洞的名字,叫林晚。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进了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我从一个最底层的程序员做起,凭着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一步步做到了项目经理的位置。
我买了房,买了车。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
我成了当年那个偷瓜的少年,想都不敢想的样子。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她。
想起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
想起她明亮的眼睛。
想起她递给我的那个西瓜。
甜的。
也是苦的。
这些年,我谈过几次恋爱。
但都无疾而终。
我心里清楚,我忘不了她。
她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拔不出来。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偷那个瓜,我们是不是就不会相遇?
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一晃,十年过去了。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我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人。
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直到那天。
公司有一个公益项目,要去一个偏远的山区,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我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队前往。
那个山区,很穷,很闭塞。
路很难走。
我们的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七八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那是一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村庄。
村里唯一的学校,是几间破旧的土坯房。
教室里,没有像样的桌椅,只有几块破木板搭成的台子。
孩子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脸蛋冻得通红,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学校的校长。
也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陈总,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抬起头。
看到了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风霜的痕迹。
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明亮,那么清澈。
是林晚。
那一刻,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时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夏天。
那个炎热的,充满了瓜果香气的午后。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千言万语。
原来,你在这里。
原来,你一直在这里。
后来,我才知道。
她父亲出事后,她拿着大学通知书,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她想去找我,但她又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我了。
她一个罪犯的女儿,怎么能去玷污天之骄子的未来?
她在北京流浪了一段时间,做过各种苦力。
后来,她偶然看到了一个招募山区支教老师的广告。
她就报名了。
她来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
一待,就是十年。
她把她所有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这里的孩子。
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她说,她没有成为钢铁,但她想为孩子们,建一座炼钢的炉子。
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听着她的讲述,泪流满面。
这个傻姑娘。
这个我找了十年的傻姑娘。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学校的操场上,看星星。
山里的星星,特别亮,特别近,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
“陈远,”她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记得。”我怎么会忘。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偷瓜的贼,胆子还真大。”她笑了。
我也笑了。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由于,我从你眼睛里,看到了不甘心。”她说,“跟你一样,我也不甘心一辈子待在那个小村子里。”
“所以,你用一个西瓜,跟我做了一笔交易。”
“是啊。”她点头,“那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划算的一笔交易。”
我们相视而笑。
所有的误会,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思念,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我留了下来。
我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和车。
我用我所有的积蓄,为孩子们建了一所崭新的学校。
有明亮的教室,有崭新的桌椅,有电脑,有图书馆。
我还请来了专业的老师。
我和林晚,也成了这里的老师。
我教孩子们数学和计算机。
她教孩子们语文和音乐。
我们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
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进步。
我找到了我从未有过的,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有一天,林晚从山下,带回来一个大西瓜。
她抱着那个瓜,笑盈盈地走到我面前。
“陈老师,瓜给你。”
我愣住了。
“干嘛?”
“你帮我浇地啊。”她指着学校后面,我们新开垦出来的一片菜地。
阳光下,她的笑容,还是像当年一样,灿烂,明媚。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西瓜,感觉像是接过了整个世界。
我看着她,认真地说:
“林晚,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
“这块地,我帮你浇一辈子。”
她哭了。
我也哭了。
我们笑着,流着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远处的教室里,传来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风吹过山谷,带来了泥土和青草的芬芳。
我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归宿。
是我漂泊了半生,最终停靠的港湾。
那个夏天,那个西瓜,改变了我的一生。
它让我遇到了一个姑娘,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让我最终,找到了回家的路。
有些遇见,是命中注定。
有些等待,终将回响。
就像那片被我们浇灌过的土地,只要你用心耕耘,总有一天,会开出最美的花,结出最甜的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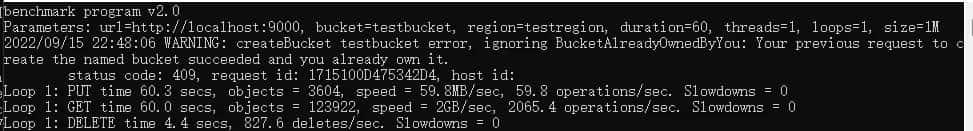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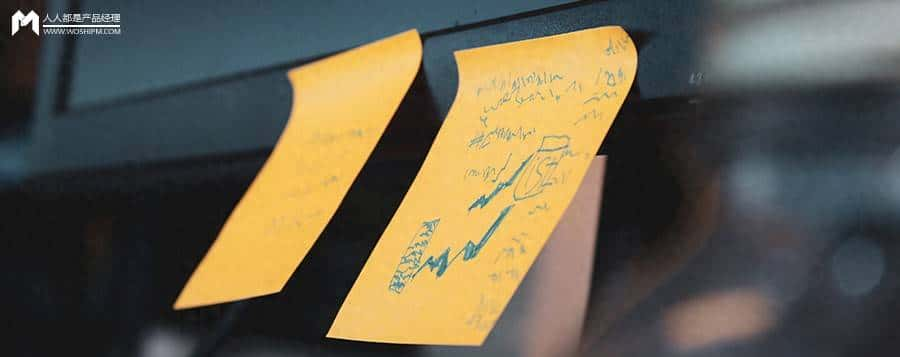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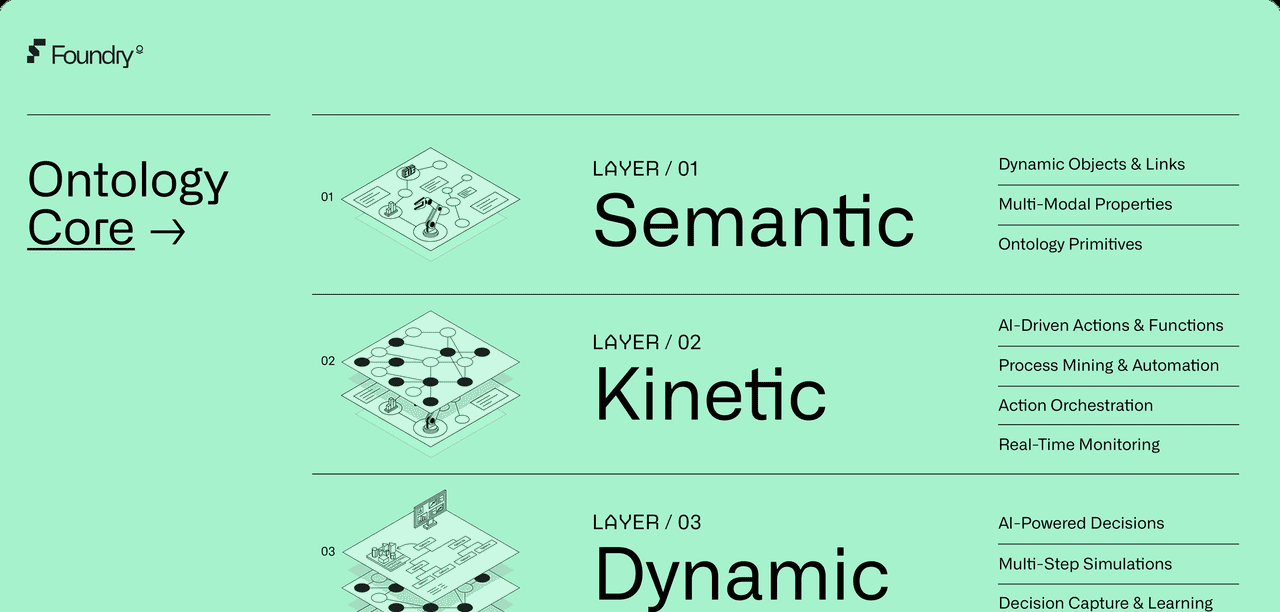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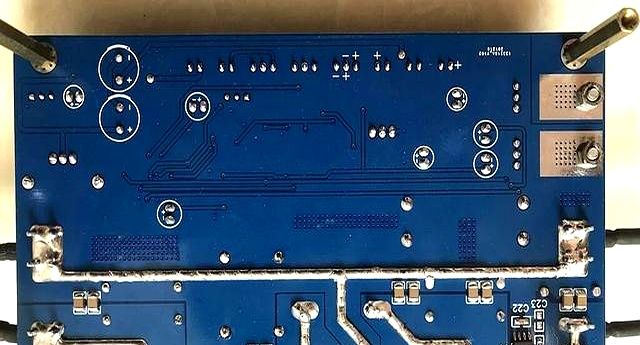
故事很好,发人深思。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