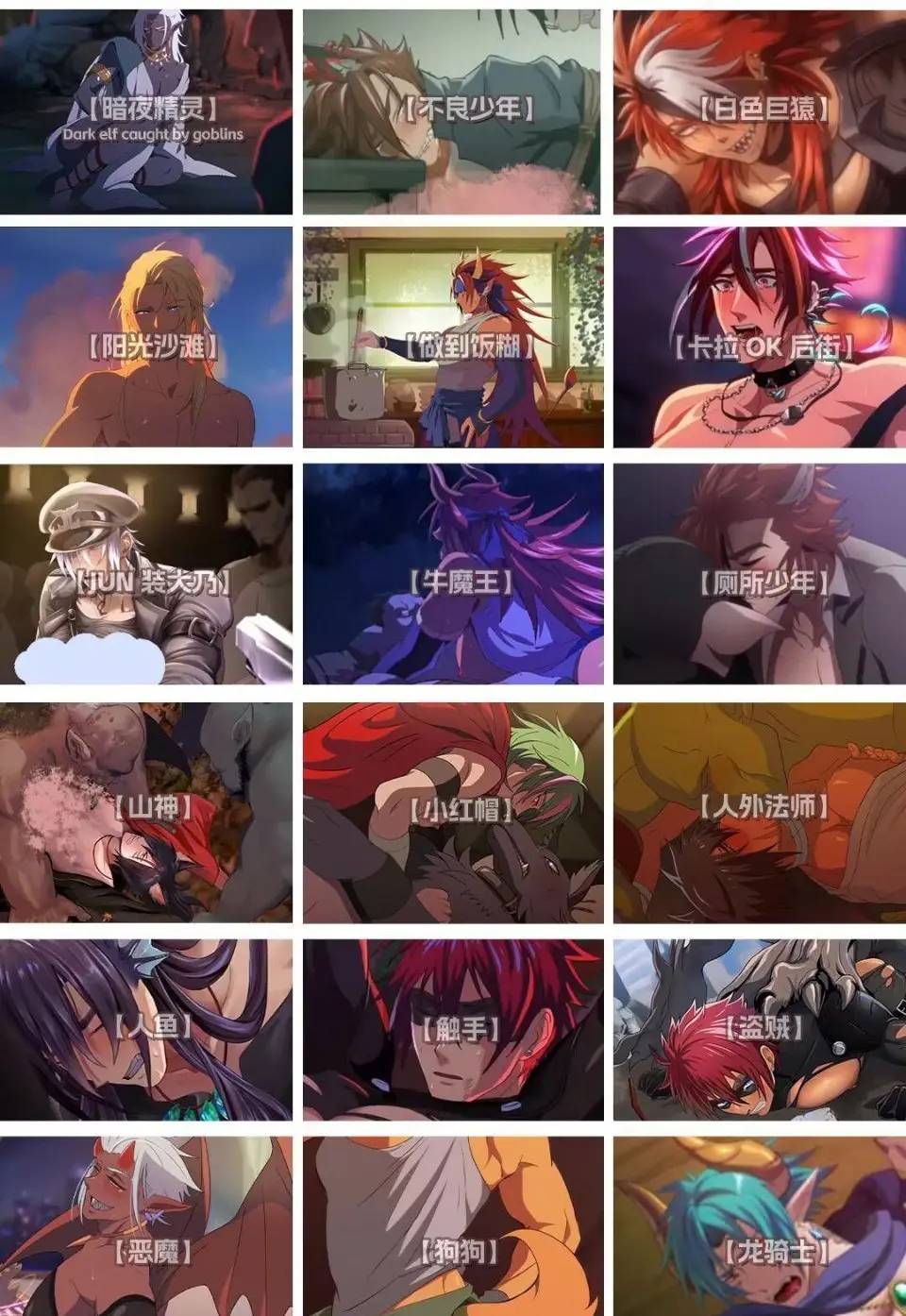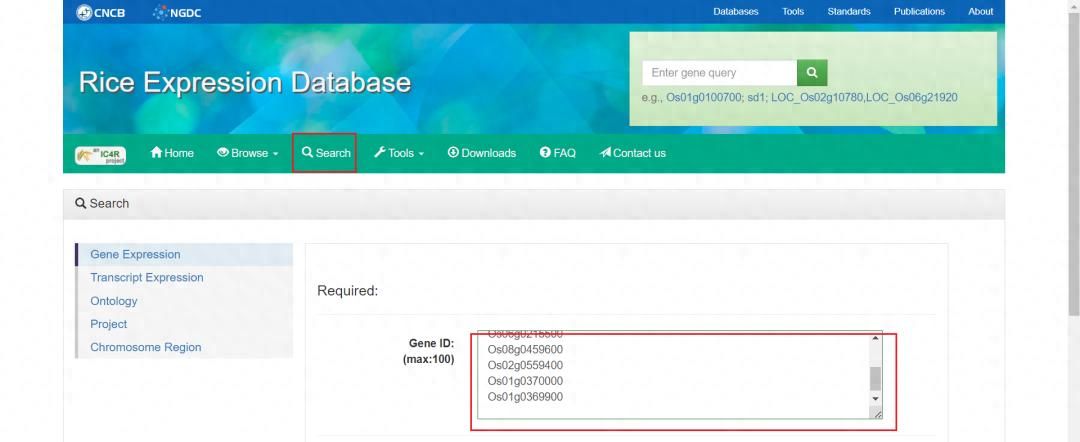再睁眼,回到继母被流寇掳走那日。我捂住弟弟的眼睛,往角落塞了塞
第一章
尘土与血腥味混杂的气息,粗暴地灌入鼻腔,呛得林默猛然睁开了眼。
入目是熟悉的、昏暗的柴房,唯一的窗户被一块破木板钉死,只有几缕惨白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照亮了空中飞舞的灰尘。
“哥,我怕……”
身边传来一个稚嫩的、带着哭腔的颤抖声音。
林默浑身一僵,如同被惊雷劈中。他缓缓转过头,看到一张布满泪痕和灰尘的小脸,那是他年仅七岁的弟弟,林风。
林风正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角,小小的身体缩成一团,惊恐地望着柴房那扇薄薄的木门。
门外,是杂乱的脚步声、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狂笑,还有器物被砸碎的刺耳声响。
这是……怎么回事?
林默的大脑一片混沌。他明明记得,自己是在五十岁那年,病死在床榻上的。弥留之际,他孑然一身,无儿无女,守着一座空荡荡的老宅,脑海里反复回荡的,却是三十多年前,这扇柴房门被撞开的巨响。
那一年,他十五岁,林风七岁。
流寇冲进村子,烧杀抢掠。他和弟弟被继母陈淑推进了这间柴房,用一把大锁从外面锁上,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他记得,当时他也是这样,紧紧抱着吓坏了的弟弟,用手捂住他的眼睛和耳朵,自己则透过门缝,眼睁睁看着那个平日里温和寡言的女人,为了引开搜寻的流寇,主动跑出去,制造声响,最终被两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拖拽着头发,消失在院门口。
他看见了她最后的眼神,那不是看向流寇的,而是望向柴房的方向。那眼神里没有怨恨,只有一种……他当年读不懂的、混杂着决绝与哀凉的复杂情绪。
从那天起,他和弟弟成了孤儿。
他带着弟弟,吃了上顿没下顿,受尽了白眼和欺辱。他把所有的爱和责任都给了这个唯一的亲人,自己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为他娶妻,给他置办家业。他以为,血浓于水,他们兄弟俩会是彼此一生的依靠。
可结果呢?
林风长大后,精明自私,对他这个长兄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他嫌弃他没本事,赚不来大钱;他抱怨他占着老宅,耽误他翻新扩建;他听信妻子的枕边风,认为他这个大伯哥是累赘。
林默五十岁生辰那天,孤零零一个人,煮了一碗长寿面。林风一家三口,就住在隔壁院子,却连一句问候都没有。他听见隔壁传来他们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妻子在夸儿子考试得了第一,林风则高兴地说要带妻儿去城里最好的酒楼庆贺。
那碗面,他吃得满嘴苦涩。
病重时,他躺在床上,不过一墙之隔,林风却一次都未曾探望。还是邻居张大娘看不过去,每日给他送些稀粥。张大娘叹着气说:“阿默啊,你那个后娘,真是个好女人啊。当年她要是没被抓走,你这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苦。我可都记得,她刚嫁过来那会儿,你和你弟都拿她当仇人看,可她呢,吃的喝的,哪样不是先紧着你们哥俩?你那双过冬的棉鞋,鞋底都磨穿了,是她熬了好几个晚上,一针一线给你纳的新底子……”
一针一线……
林默的记忆,像是被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
他想起来了。陈淑刚嫁过来时,他和弟弟对她充满敌意。父亲去世得早,他们觉得这个女人是来抢他们爹、抢他们家的。他们故意打翻她做的饭,把虫子放进她的被窝,用最难听的话骂她。
可她从不生气,只是默默地收拾残局,默默地为他们缝补衣服,默默地在深夜里,坐在油灯下,为他们纳鞋底。
他十五岁那年,脚长得快,一双鞋穿了两年,鞋头已经破了洞,露出冻得通红的脚趾。是陈淑,把家里仅有的一点棉花,都絮进了给他做的新棉鞋里。而她自己的鞋,鞋帮上补丁摞着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流寇来的前一天晚上,她把那双崭新的棉鞋放在他床头,轻声说:“阿默,天冷了,快换上吧。脚暖和了,身上才有劲儿。”
他当时只是冷冷地“嗯”了一声,连句谢谢都没说。
而那双鞋,后来在他带着弟弟逃难的路上,遗失了。
他这一生,都在为弟弟付出,以为这是长兄的责任,是血脉的羁绊。直到死前,他才幡然醒悟,那个与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继母,才是那个真正给予他温暖,却被他亲手推开的人。
他亏欠了她。
这份愧疚,沉重得让他至死都无法释怀。
“哥!他们要进来了!”
林风的哭喊声将林默的思绪猛地拽回现实。
“哐当!”一声巨响,柴房的门被重重地踹了一脚,门板剧烈地颤抖,木屑簌簌落下。
林默的心脏狂跳起来。
一样的场景,一样的声音,一切都和记忆中分毫不差。
他不是在做梦。他真的……回来了。回到了那个让他悔恨终生的下午!
第二章
重活一世,他绝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林默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前世五十年的风霜和悔恨,此刻都化作了冷静与决绝。
“别怕!”他压低声音,对怀里的弟弟说。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镇定,让瑟瑟发抖的林风下意识地安静了一些。
上一世,他就是这样抱着弟弟,躲在柴火堆后面,捂住他的眼睛,祈祷流寇不要发现他们。他的选择是“躲”,是消极的等待,最终的结果是牺牲了陈淑,换来了他们兄弟俩的苟活。
可那样的苟活,值得吗?
用一个真心待他们好的人的性命,去换一个日后会视他如敝屣的白眼狼的安稳?
林ou's mind raced. He couldn't just sit here. The bandits were brutaland disorganized. They were after valuables and food, and sometimes,people. He remembered from his past life that they didn't stay long inany one house. Their goal was quick plunder. If he could create asituation where they thought this house was already looted or not worththeir time, they might leave.
The lock on the outside was their protection, but also their prison.Chen Shu had locked it to keep them safe, but it also meant theycouldn't get out to help.
“哐!哐!”
The door was kicked again, harder this time. The wood groaned, and acrack appeared near the latch.
There was no time to hesitate.
“小风,听着,”林默抓住弟弟的肩膀,让他看着自己,“目前,不是哭的时候。你要像个男子汉。哥哥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清楚吗?”
林风被他严肃的眼神镇住了,含着眼泪,用力地点了点头。
林默迅速扫视这间狭小的柴房。柴火堆、一个破旧的石磨、几只装杂物的麻袋,还有一个通向后院菜地的、被杂物堵死的小气窗。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那个石磨上。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中飞速成形。
“小风,去,躲到那堆最里面的柴火后面,用麻袋盖住自己,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声,也不要出来,记住了吗?”
“哥,那你呢?”林风的眼中满是恐惧。
“哥哥要保护我们,保护……娘。”林默顿了一下,那个陌生的称呼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些生涩,却异常坚定。
他不再多言,将林风用力塞进柴房最深的角落,用几捆干柴和一个破麻袋将他严严实实地盖住。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开始推动那个沉重的石磨。
前世的他,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瘦弱,力气也不大。但此刻,他的身体里仿佛注入了一股来自未来的、不屈的灵魂。他的牙关紧咬,额头上青筋暴起,手臂上的肌肉由于过度用力而酸痛颤抖。
石磨在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摩擦声。
“哐啷!”
就在这时,柴房的门终于被踹开了。
两个手持砍刀的流寇冲了进来,满脸的凶悍与不耐。
“妈的,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原来是个破柴房!”其中一个络腮胡骂骂咧咧地说。
另一个鹰钩鼻的眼神一扫,立刻就看到了正在奋力推着石磨的林默。
“嘿,这儿还有个小崽子!”鹰钩鼻眼中闪过一丝狞笑,“小子,家里大人呢?值钱的东西藏哪儿了?快说!”
林默停下动作,喘着粗气,胸膛剧烈地起伏。他没有看那两个流寇,而是将目光死死地盯在他们身后的院子里。
他看到了。
陈淑正被另一个流寇抓着头发,她拼命挣扎,脸上却毫无惧色。当她看到柴房门被踹开,两个流寇堵在门口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当她的目光与林默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她愣住了。
她预想过林默会害怕,会哭泣,会躲起来。但她没想过,他会站在那里,像一头被激怒的小狼,用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充满决绝和保护欲的眼神看着她。
“阿默……”她无声地动了动嘴唇。
就是目前!
林默猛地一咬牙,将石磨奋力推向门口!
他的目的不是砸人,他知道自己没那个准头和力气。他的目的是制造混乱和障碍!
沉重的石磨带着巨大的声响,轰然撞在门框上,然后侧翻在地,正好堵住了大半个门口。
“操!你个小兔崽子找死!”络腮胡反应过来,怒吼一声,举刀就要冲进来。
但石磨挡住了他的路,他只能侧着身子往里挤。
这短暂的延误,就是林默用生命争取来的机会。
他转身,扑向那个被杂物堵死的气窗,用肩膀狠狠撞了上去。
“砰!”
朽坏的木窗框应声而碎。
“娘!快跑!从后面跑!”林默用尽全身力气,声嘶力竭地喊道。
这是他第一次,叫她“娘”。
院子里的陈淑浑身一震,眼眶瞬间就红了。她不知道这个一向对她冷若冰霜的继子为何突然转变,但她看到了他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急切。
求生的本能和一个母亲的本能,在这一刻战胜了恐惧。
她猛地弯腰,张口狠狠咬在抓住她头发的那个流寇的手腕上。
“啊!”那流寇吃痛,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陈淑想也不想,转身就往后院的方向疯跑。
“抓住她!”鹰钩鼻见状大急,也顾不上林默了,转身就要去追。
林默已经从气窗里翻了出去,他落地滚了一圈,爬起来就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那个刚从柴房里挤出来的络腮胡的腿。
石头不大,但砸得很准。络腮胡“嗷”地一声,腿一软,险些跪倒在地。
“小王八蛋,老子宰了你!”
愤怒的流寇们彻底被激怒了。
林默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自己身上。他没有回头看陈淑是否已经跑远,而是拔腿就往与后院相反的方向,朝着村口的大路上狂奔。
他要引开他们!
他的体力远不如这些成年人,但他熟悉这里的地形。他专挑那些狭窄的、布满障碍物的小巷子钻。
身后的叫骂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
林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肺部像火烧一样疼。
他知道,自己可能跑不掉了。
但只要陈淑和小风能活下来,就够了。
前世,他苟活了三十五年,每一天都活在愧疚的囚笼里。这一世,哪怕只能多活这短短一刻,能用自己的命换回她的命,他亦无悔。
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力竭,即将被追上的时候,前方巷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呼喊。
“官兵来了!官兵来了!快跑啊!”
追赶他的那几个流寇脸色大变,对视一眼,顾不上再追他这个小鬼,咒骂了一句,立刻调头,仓皇逃窜。
林默腿一软,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得救了。
更重大的是,他的计划,成功了。
第三章
官兵的到来很快平息了村子里的混乱。
流寇们来得快,去得也快,只留下一片狼藉和村民们的哭喊声。
林默顾不上休憩,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家的方向跑去。他的心脏由于紧张和期待而剧烈地跳动着。
成功了吗?她和小风都安全吗?
当他冲进自家那个破败的院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陈淑正站在柴房门口,焦急地张望着,她的头发散乱,脸上还有一道被树枝划破的血痕,但人是完好无损的。
而在她身边,林风正抱着她的腿,放声大哭。
看到林默回来,陈淑的眼睛“唰”地一下亮了,她快步冲上来,一把抓住林默的胳膊,上下打量着他,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阿默!你……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林默摇了摇头,目光落在她脸上那道血痕上,又看了看她被流寇抓得红肿的手腕,心中五味杂陈。
“我没事。”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哥!”林风也哭着跑过来,紧紧抱住他的腿,“我好怕,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林默摸了摸他的头,心中却没有了前世那种怜爱和心疼。他只是平静地说:“我让你躲好,你出来做什么?”
林风被他问得一愣,抽噎着说:“我……我听到外面没声音了,就……就出来了……”
陈淑连忙解释道:“不怪他,是我把他叫出来的。我跑出去后,躲在后山坡上,看到流寇被官兵惊走,就赶紧回来了。我看你没回来,急得不行,就想让小风出来,问问你往哪边跑了。”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后怕和担忧,那份真切的关心,让林默的心头一暖。
前世,他从未体会过这种失而复得的庆幸。流寇走后,他从柴火堆里出来,面对的是一个被洗劫一空的家,和一个永远也回不来的人。他和小风抱头痛哭,从此,这个家便只剩下冰冷的绝望。
而目前,家虽然也乱了,但最重大的三个人,都在。
这便足够了。
“娘,你受伤了。”林默的目光落在陈淑脸上的伤口,伸出手,想要触碰,却又在半空中停住了。
那一声“娘”,让陈淑的身体再次僵住。
她怔怔地看着林默,眼眶里迅速积满了水汽。
这个称呼,她等了太久了。自从嫁到林家这两年,两个继子从未给过她好脸色。她任劳任怨,把他们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换来的却是冷漠和排斥。她以为,这辈子都听不到他们叫她一声娘了。
可今天,就在刚才,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是这个一向最倔强的继子,用一声嘶哑的“娘”,给了她逃生的勇气。
而目前,他又叫了她一声。
“我……我没事,小伤,不碍事的。”陈淑连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声音哽咽,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们都没事,就好,就好……”
看着她这副样子,林默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他想,自己前世真是个混蛋。
第四章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所幸本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仅有的一点存粮被抢走之外,没有太大的损失。
陈淑很快就收拾好了情绪,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屋子。她检查了一下水缸,发现水还在,便先烧了热水,让两个孩子擦洗一下身上的灰土。
林默默默地帮着她收拾。他将倒下的桌椅扶起来,把散落一地的杂物归置好。他的动作很沉稳,完全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陈淑好几次都想开口问他为什么突然变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怕一问,这一切又会变回原样。目前的林默,让她感到陌生,却也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晚饭,是陈淑用藏在地窖里的最后一点红薯,煮的一锅稀粥。
粥很稀,几乎能照出人影,但三个人围在小小的饭桌前,喝得却异常香甜。
林风大致是吓坏了,一晚上都黏着陈淑,吃饭的时候也要挨着她坐。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挑三拣四,一口一口地喝着粥,小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依赖。
林默看着这一幕,心里很平静。
他知道,一场危难,彻底改变了他们这个重组家庭的关系。至少,在林风心里,陈淑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外人”,而是和哥哥一样,可以保护他的人。
吃完饭,陈淑找出针线和草药,就着昏暗的油灯,小心翼翼地给林默处理他逃跑时被刮伤的胳膊。
她的动作很轻,一边上药,一边不停地吹着气,仿佛这样就能减轻他的疼痛。
“阿默,”她终于还是忍不住,轻声开了口,“今天……谢谢你。”
林默摇摇头:“应该我谢你。如果不是你把我们锁在柴房,后果不堪设想。”
陈淑的眼圈又红了:“可我差点……差点就害了你。我当时只想着让你们躲起来,没想到你……”
“我是家里的长子,保护你们是我的责任。”林默打断了她的话,语气平静而坚定。
这话,他前世也对自己说过无数遍。但那时的“你们”,只包括他和林风。而目前,这个“你们”里,多了一个她。
陈淑低着头,一滴眼泪落在林默的手背上,滚烫。
她快速地擦掉,然后从床头的针线笸箩里,拿出一双崭新的棉鞋。
“这个……前天就做好了,一直没好意思给你。”她把鞋子递到林默面前,有些局促地说,“你试试,看合不合脚。”
林默看着那双鞋,心脏像是被一只温暖的手紧紧攥住。
就是这双鞋。
前世,他冷漠地收下,第二天就由于逃难而弄丢了。这一世,它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他的手上。
鞋面是深蓝色的粗布,针脚细密而均匀。鞋底是她用碎布一层层黏合,再用麻线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厚实而坚固。他甚至能想象出,她是如何在油灯下,眯着眼睛,一针一针,熬过一个个夜晚的。
“娘,”林默接过鞋,郑重地放在膝上,抬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后来,这个家,我来撑着。”
他没有说太多煽情的话,但这个承诺,却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分量。
陈淑愣愣地看着他,看着他那双不再是少年般桀骜,而是充满了沉稳和担当的眼睛,终于忍不住,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这两年的委屈、辛酸、孤独,在这一刻,仿佛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林默没有去安慰她,只是静静地坐着。
他知道,她需要哭一场。
而他,则需要用余生的时间,去弥补他前世所犯下的过错。
第五章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默就起了床。
他穿上了那双崭新的棉鞋,不大不小,刚刚好。鞋底厚实,踩在地上感觉特别踏实,一股暖意从脚底一直蔓延到心里。
他先是去村里转了一圈,打探了一下情况。
这次来的流寇是一股散兵游勇,被官兵一冲就散了,暂时应该不会再来。但村子里人心惶惶,不少人家都动了去城里投奔亲戚的心思。
林默知道,乱世之中,哪里都不是真正的安全港。他们无亲可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
家里的粮食被抢光了,这是眼下最大的难题。
回到家,陈淑和林风也已经起来了。陈淑正在发愁,看到林默,便忧心忡忡地说:“阿默,家里的米缸空了,这可怎么办?”
“娘,你别急,我来想办法。”林默安慰道。
他让陈淑和林风待在家里,自己则背上一个破旧的背篓,拿上砍柴刀,往后山走去。
村子靠山,山里物产还算丰富。目前是初冬,虽然没什么野果,但还能找到一些可食用的根茎和野菜,运气好的话,还能设个陷阱套只野兔或山鸡。
前世逃难的路上,为了填饱肚子,他练就了一身在野外求生的本领。辨认植物、设置陷阱,这些对他来说都驾轻就熟。
他在山里转了大半天,挖了小半篓的葛根和一些还能吃的野菌,还在一处隐蔽的山涧旁,发现了一排野兔的脚印。
他没有急着下套,而是仔细观察了地形,然后用树枝和藤蔓,做了一个简单的活套陷阱,巧妙地伪装起来。
做完这一切,天色已经不早了。
他背着背篓下山,路过村东头的王屠夫家时,被王屠夫叫住了。
“哟,这不是林家大小子吗?进山了?”王屠夫是个热心肠的汉子。
“是啊,王叔,家里没粮了,进山找点吃的。”林默停下脚步,客气地回答。
王屠夫探头看了看他的背篓,叹了口气:“唉,这世道……对了,你等等。”
他说着,转身进了屋,不一会儿,提着用油纸包着的一小块肉出来,塞到林默手里。
“王叔,这可使不得!”林默连忙推辞。
“拿着!就当叔送给你们压惊的!”王屠夫把脸一板,“你娘是个好女人,你们哥俩也争气。昨天那事儿,我可都听说了,你小子,有种!像你爹!”
林默心里一暖,不再推辞,郑重地道了谢。
他知道,这是他昨天拼死保护家人的行为,为自己赢得的尊重。
第六章
回到家,陈淑看到他背篓里的东西,又惊又喜。当她看到那块肉时,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这是哪来的?”
“王屠夫给的。”林默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陈淑的眼圈又红了。她喃喃道:“你王叔,真是个好人……”
林风闻到肉味,早就馋得直流口水,围着那块肉直打转。
晚饭,陈淑用葛根粉混着野菜煮了糊糊,又把那块肉切了一半,炖了一小锅肉汤。
浓郁的肉香味,飘满了整个屋子,这是他们家许久未曾有过的味道。
林风喝着肉汤,吃得满嘴是油,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陈淑把肉都挑给了两个孩子,自己只喝汤。林默把自己碗里的肉夹了一块给她,说:“娘,你也吃。”
陈淑连忙推回来:“不了不了,你们吃,你们正在长身体。”
“家里不能没有顶梁柱,你也要吃。”林默不容置疑地把肉又夹了回去,“后来,肉会有的,白米饭也会有的。”
他的话,让陈淑的动作停住了。她看着碗里的肉,又看看林默,最终没有再推辞,小口地吃了起来。
吃完饭,林默开始为家里的长远生计做打算。
光靠山里那点东西,不是长久之计。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定的赚钱门路。
他想起前世的一些事情。这次流寇之乱后,朝廷为了稳定地方,加强了对附近几座城池的管控,并重开了几条荒废已久的商路。大致在半年后,会有第一批商队从他们村子附近经过。
商队的出现,意味着机会。
他们需要向导,需要脚夫,也需要采买沿途的补给。
而他们村子附近的山里,有一种特殊的药材,叫做“青风藤”,有祛湿活血的功效,是制作跌打损伤药膏的主料。只是由于山路难行,很少有药商愿意进来收购,所以村里人也只当它是普通的藤蔓,没人重点关注。
林默前世曾经在一家药铺当过学徒,认识这种药材。
如果他能提前采摘、晾晒好一批青风藤,等到商队经过时,必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第七章
接下来的日子,林默的生活变得异常规律和忙碌。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去山里检查陷阱。他的运气不错,接连几天,套到了一只野兔和两只山鸡。
这些猎物,他没有全部留下。他让陈淑把肉处理好,一部分自家吃,改善伙食,另一部分则送到王屠夫和之前接济过他们家的邻居那里。
他知道,乱世之中,邻里关系就是一张无形的保护网。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送完东西,他便一头扎进深山,去寻找和采摘青风藤。
这项工作很辛苦。青风藤大多生长在陡峭湿滑的岩壁上,采摘起来十分危险。林默每天都弄得一身泥土,手掌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旧的血泡破了,又长出新的老茧。
陈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每天都会准备好热水和干净的衣服,等林默回来。晚上,就在油灯下,一边帮他处理手上的伤口,一边默默地掉眼泪。
“阿默,太危险了,咱们不去了好不好?娘去给大户人家洗衣裳,也能赚点嚼谷。”
“娘,你放心,我有分寸。”林默总是这样安慰她,“你做的饭,是我在山里最大的盼头。”
他知道陈淑是心疼他,但他不能停下来。他不仅要让他们活下去,还要让他们活得好。
林风也在这段时间里,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娇气和自私。他看到哥哥每天辛苦劳累,看到娘亲每天忧心忡忡,这个七岁的孩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会主动帮陈淑扫地、喂鸡。陈淑做饭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安安静静地拉着风箱。林默从山里回来,他会立刻端上一碗热水。
有一天,林默采药回来,发现自己那双宝贝得不行的棉鞋,鞋面上沾的一点泥巴,被擦得干干净净。
他问是谁做的,林风红着脸,小声说:“我……我看见鞋脏了,就用布擦了擦。”
林默看着他,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第一次,露出了一个真心的笑容。
这个弟弟,虽然前世不堪,但这一世,在他七岁的时候,还是个可以被教导的好苗子。只要用心引导,他未必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家庭的氛围,在这样辛苦却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变得越来越温馨。
林默采回来的青风藤,被陈淑仔细地清洗、切段、晾晒在院子里。很快,小小的院子就摆满了药材,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香。
村里人见了,都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林默只说是普通的藤蔓,晒干了冬天当柴烧。
不是他信不过乡亲,而是他知道,怀璧其罪。在商队到来之前,这个秘密,必须守住。
第八章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初冬的寒意渐渐被严冬的酷寒所取代。
靠着林默的努力,他们家的日子不仅没有变得更糟,反而渐渐好了起来。
陷阱里偶尔的猎物,让他们不至于断了荤腥。林默用猎物换来的粮食和布匹,让家里的米缸满了,也让陈淑和林风都穿上了厚实的冬衣。
林默自己,却依旧是那身打着补丁的旧衣服。陈淑要给他做新的,他总是说不急。
他把所有能省下来的钱,都攒了起来。
这天,他去镇上,花了三十个铜板,买了一口二手的铁锅和一些调味料。
陈淑不解:“家里有锅,怎么又买一口?”
林默笑了笑,神秘地说:“娘,我准备做点小买卖。”
第二天一早,他将之前留下的兔肉和鸡肉剁成肉糜,又将积攒下来的骨头熬成高汤,然后和着葛根粉和野菜,用新买的铁锅,在村口的大树下,支起了一个小摊子。
他卖的,是肉羹。
骨汤做底,肉糜提香,葛根粉增加稠度,再撒上一点点盐和葱花。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对那些下地干活的村民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一碗三文钱。
这个价格不贵,一碗下肚,浑身都暖洋洋的。
一开始,大家只是好奇。后来,有人试着买了一碗,立刻就被那鲜美的味道征服了。
一传十,十传百。
林默的小摊子,生意竟然出奇地好。
陈淑和林风也来帮忙。陈淑负责收钱,林风则负责给大家拿碗。一家三口,配合得十分默契。
林风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帮家里做事,小脸蛋冻得通红,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的光。
收摊的时候,林风捧着装钱的小布袋,激动地对林默说:“哥!我们今天赚了六十文钱!”
六十文钱,对于他们这个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林默摸了摸他的头,说:“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赚的。”
他将布袋交给陈淑:“娘,钱你收着。”
陈淑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布袋,手都在抖。她看着林默,又看看林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她觉得,日子,真的有盼头了。
第九章
肉羹摊的生意,让林家的生活彻底走上了正轨。
林默不再需要每天都冒险进山,他隔几天去检查一次陷阱,采摘一些青风藤,其余的时间,就和陈淑一起,经营这个小小的摊子。
家里的积蓄,从几十文,到几百文,再到一贯钱。
看着钱串上越来越多的铜钱,陈淑晚上睡觉都觉得不踏实,总是翻来覆去地检查藏钱的瓦罐。
林默看着她这副样子,觉得好笑又心酸。这个女人,真是苦怕了。
他把钱分成两份,一份交给陈淑,作为家里的日常开销,让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要再省着。另一份,他自己收着,作为启动资金。
他知道,一个小小的肉羹摊,只是权宜之计。他真正的目标,是等商队到来。
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村子里终于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振奋的消息。
官府贴出告示,由于地方靖平,将重开自南向北的“云门商道”。而这条商道,正好要从他们村子东边的官道上经过。

村子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的人准备开个小茶寮,给过路的客商歇歇脚。有的人准备编些草鞋、竹器去卖。
而林默,则开始了他计划的最后一步。
他用自己攒下的钱,去镇上最好的药铺,买了几味常见的辅药,又买了一个小小的石臼。
回到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将晾晒了大半个冬天的青风藤,按照前世在药铺里学来的方子,和那些辅药混合在一起,用石臼捣成药粉,再用麻油和蜂蜡调和,制成了一罐罐墨绿色的药膏。
这种药膏,对于长途跋涉、容易跌打损伤的商队伙计和护卫来说,是极好的常备药。
他做得很小心,每一次的配比,都严格按照记忆中的方子来。
陈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她没有多问。她只是默默地支持着他,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终于,在初夏的一个清晨,村口传来了喧闹声。
第一支商队,到了。
第十章
商队的规模比林默想象的还要大。
绵延不绝的马车,驮着各色货物,精壮的护卫骑着高头大马,护卫在两翼。商队管事的,则穿着体面的绸衫,脸上带着精明的笑容。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村民们拿出自家的东西,涌到官道两旁,希望能做成一笔买卖。
林默没有去凑这个热闹。
他等到商队在村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开始埋锅造饭的时候,才背上一个装着十几罐药膏的小包袱,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
他没有直接去叫卖,而是找到了商队的马夫。
这些马夫,常年跟牲口打交道,手上脚上难免有些磕碰损伤。
林默客气地递上一罐药膏:“这位大哥,看您手上这茧子,是常年拉缰绳磨的吧?我这儿有自家配的药膏,对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有奇效。您要不嫌弃,抹上一点试试?不要钱。”
那马夫见他年纪不大,说话却很老成,便半信半疑地接了过去。
他打开罐子,一股清凉的药香扑鼻而来。他挖了一点,抹在自己被缰绳磨得红肿的手腕上。
药膏抹上去,清清凉凉的,火辣辣的疼痛感,竟然真的缓解了不少。
“嘿!你这药,还真有点门道!”马夫惊讶地说。
很快,其他的马夫和伙计也围了过来,纷纷讨要试用。
林默来者不拒,每一罐都大方地让他们试。
他的药膏,效果是实打实的。很快,就赢得了这些底层伙计的交口称赞。
这时,一个管事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皱着眉问:“吵吵嚷嚷的,在干什么?”
一个伙计连忙把药膏递上去,兴奋地说:“刘管事,您看这药!我这扭伤的脚踝,抹上之后,舒服多了!”
刘管事接过药膏,闻了闻,又看了看色泽,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自己也常年在外奔波,对这些跌打损伤的药,也算识货。
他看向林默,问:“小子,这药膏是你做的?怎么卖?”
林默知道,正主来了。
他不卑不亢地回答:“回管事,这药膏是我祖传的方子。一罐,五十文。”
“五十文?”旁边的人都抽了口冷气。
镇上最好的金疮药,也不过这个价钱。
刘管事却没觉得贵。他掂了掂手里的药膏,说:“你这药,效果不错。但五十文,贵了些。这样,我全要了,三十文一罐,如何?”
林默摇了摇头。
“刘管事,我这药,用料都是山里采的,炮制也费工夫。五十文,一文都不能少。”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商队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兄弟们难免有个磕碰。我这药,不仅能止痛,还能防伤口发炎。您算算,是兄弟们的健康重大,还是这几文钱重大?”
他的话,说得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刘管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半大少年,眼神沉稳,谈吐从容,完全不像个普通的农家小子。
他沉吟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好!你这小子,有点意思。你这儿有多少,我全要了!”
林默心中一喜,但面上不动声色。
他将带来的十几罐药膏都卖给了刘管事,净赚了七百多文钱。
这几乎是他们家卖一个月肉羹的收入。
刘管事付了钱,又对他说:“小子,你的药不错。下一批,我们还要。三个月后,我们还会经过这里。你能准备多少?”
“只要管事您要,多少都有。”林默自信地回答。
“好!一言为定!”
第十一章
第一笔生意成功,让林默信心大增。
他回到家,把赚来的钱交给陈淑时,陈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看着那一串沉甸甸的铜钱,又看看林默,只觉得自己的这个继子,像是脱胎换骨了一般。他不仅撑起了这个家,还在用他的智慧和能力,带着这个家,走向一个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未来。
有了稳定的销路,林默开始扩大生产。
他不再满足于自己一个人采药。他找到了村里几个老实可靠、腿脚利索的年轻人,教他们辨认青风藤,然后以每斤五文钱的价格,收购他们采来的药材。
这个价格,比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天农活赚得还多。
一开始,大家还半信半疑。但当林默当场用现钱结了第一批药材的款后,所有人都沸腾了。
很快,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加入了采药的队伍。
林默则在家里,带着陈淑和林风,一起炮制药膏。
他买来了更多的石臼和铁锅,把制作药膏的流程,分成了好几个步骤。陈淑负责清洗和晾晒,林风负责捣药,他自己则负责最关键的配药和熬制。
一家人,忙得热火朝天,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林风在捣药的过程中,渐渐对这些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默便把自己知道的药理知识,一点一点地教给他。
他希望这个弟弟,这一世能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而不是像前世那样,只会依附于他,最终变成一个废人。
三个月后,刘管事的商队如期而至。
这一次,林默准备了足足五百罐药膏。
刘管事看到堆成小山一样的药膏,惊讶得合不拢嘴。他检查了药膏的品质,和上次一样,甚至更好。
他二话不说,当场就以五十文一罐的价格,全部收购。
五百罐,就是二十五贯钱!
这笔巨款,让整个村子都震动了。
林默当着所有人的面,给采药的村民结清了工钱,又拿出两贯钱,交给了村长,说是用来修缮村里的道路和祠堂。
他的举动,赢得了所有村民的尊敬和爱戴。
从此,林默在村子里的地位,彻底不一样了。大家不再当他是个半大孩子,而是把他当成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的主心骨。
第十二章
钱,是英雄胆。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林默的计划,也开始变得更大胆。
他不再满足于只做药膏这一种生意。他知道,云门商道一旦稳定下来,往来的客商会越来越多,他们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
他用赚来的钱,在村口官道旁,买下了一块地。
然后,他请来村里的工匠,开始大兴土木。
他要盖的,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一个集住宿、餐饮、货物中转于一体的……客栈。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人看来,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陈淑第一个表明了担忧:“阿默,盖这么大的房子,得花多少钱啊?万一……万一后来没客商来了,可怎么办?”
“娘,你放心。”林默耐心地跟她解释,“商道开了,只会越来越繁华。我们目前抢先一步,就能占得先机。等人人都看到这里能赚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站稳脚跟了。”
他详细地跟陈淑描绘了客栈未来的蓝图。
一楼做大堂,提供饭菜茶水。二楼做客房,给过路的客商住宿。后院建一排仓库,可以帮客商临时存放货物。还要建一个宽敞的马厩,帮他们喂养马匹。
他的描述,让陈淑听得一愣一愣的。她虽然不懂这些,但她从林默自信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强劲的力量。
“好,娘信你。”最终,她选择了无条件地支持。
客栈的建造,成了一件大事。
林默亲自画图纸,监督施工。他把前世看到的一些建筑布局和经营理念,都融入了进去。列如,他设计的客房,有通铺,也有单间,满足不同消费水平的客人的需求。他设计的厨房,卫生和流程都思考得十分周到。
村里的人,见林默家又要搞大动作,都议论纷纷。有羡慕的,也有等着看笑话的。
林默一概不理。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客栈的建设中。
林风也成了他的小跟班。他不再满足于捣药,而是对盖房子产生了兴趣。他每天跟在工匠师傅后面,问这问那,像块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知识。
林默乐于见到他的这种转变。
他告知林风:“读书识字固然重大,但安身立命的本事,更重大。你要多看,多学,多想。后来这家业,哥还要指望你一起打理。”
“嗯!”林风用力地点头,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第十三章
半年后,一座青砖黛瓦、两层小楼的客栈,在村口拔地而起。
林默给客栈取名“平安客栈”。
寓意很简单,他希望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平平安安。也希望他的家,能永远平安和顺。
客栈开业那天,林默没有搞什么隆重的仪式,只是放了一串鞭炮。
王屠夫、村长和一些交好的邻居都来道贺。
刘管事的商队,也恰好在这一天抵达。
看到这座崭新的客栈,刘管事大吃一惊。他没想到,短短半年不见,那个卖药膏的少年,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林默老弟,你这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刘管事拍着林默的肩膀,由衷地赞叹道。
“刘大哥说笑了,都是混口饭吃。后来还请刘大哥多多关照。”林默笑着说。
他将刘管事和商队的人,都请进了客栈。
宽敞明亮的大堂,擦得锃亮的桌椅,干净整洁的后厨,还有陈淑亲手炒的几样拿手小菜,都让这些走南闯北的商队成员,感到耳目一新。
尤其是当他们住进二楼的客房,发现床铺虽然简单,但被褥都是新弹的棉花,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时,更是赞不绝口。
“林老弟,你这客栈,是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住过最舒心的!”刘管事感慨道。
当天晚上,刘管事的商队,就成了平安客栈的第一批客人。
住宿、吃饭、喂马,再加上采购了一大批药膏,一天下来,就给林默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平安客栈的成功,彻底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商道的日益繁华,平安客栈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喜爱在这里歇脚。他们不仅喜爱这里的干净舒服,更喜爱这里的诚信和公道。
林默从不欺客,饭菜价格公道,住宿童叟无欺。他还免费为客商提供热水和一些简单的缝补工具。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平安客栈”的名声,渐渐地在云门商道上传了开来。
第十四章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林默在镇上买了宅子,把家搬到了镇上。但他没有放弃村里的客栈,而是雇了几个老实可靠的村民帮忙打理,自己则每隔几天回去看看。
陈淑彻底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她不用再为生计发愁,每天含饴弄孙……哦不,是带着林风,过上了富足安逸的生活。
林默给她买了许多新衣服和首饰,但她最常穿的,还是那几件自己做的粗布衣裳。她总说,穿着踏实。
林风被林默送去了镇上最好的学堂读书。
但林风对四书五经的兴趣不大,反而对算术和经营之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天赋。
他每天放学,就跑到客栈的账房,帮着账房先生算账。没过多久,客栈的流水和账目,他已经能算得清清楚楚,甚至还能提出一些节约成本的提议。
林默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他知道,这个弟弟,已经彻底摆脱了前世的影子,正在朝着一个可靠的、能独当一面的方向成长。
这天,林默从外面回来,看到林风正趴在桌子上,对着一本账本,愁眉苦脸。
“怎么了?”林默走过去问。
“哥,”林风抬头,指着账本说,“我算了一下,我们客栈的生意虽然好,但利润的大头,还是来自你的药膏。其他的,都只是蝇头小利。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拓展一些别的生意。”
林默赞许地点了点头:“哦?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过了,”林风的眼睛亮了起来,“我们守着云门商道,最大的优势,就是‘流通’。南边的丝绸、茶叶,运到北边,价格能翻好几倍。北边的皮货、药材,运到南边,也同样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组建一个商队呢?”
林默看着弟弟,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欣慰。
他想到了自己前世,那个只会伸手向他要钱,只会抱怨他没本事的弟弟。再看看眼前这个,眼神清亮,思路清晰,已经开始为家族的未来谋划的少年。
他知道,自己重活一世,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做到了。
他不仅救了陈淑,也“救”了林风。
“你的想法,很好。”林默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过,组建商队,不是一件小事。需要人手,需要本钱,更需要打通各地的关节。这件事,不急,我们可以慢慢来。”
“嗯!我听哥的!”林风重重地点头。
第十五章
就在林默的生意蒸蒸日上,家庭和睦美满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刘管事的商队再次来到平安客栈。
席间,刘管事面带忧色地对林默说:“林老弟,跟你说个事。最近道上不太平,出了伙专抢劫商队的悍匪,下手极狠。我们这次,也是绕了远路,才躲过去的。”
林默心中一凛:“官府不管吗?”
“怎么不管?派兵围剿了好几次,但那伙悍匪对地形极为熟悉,每次都能逃掉。据说,他们的头目,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林默安慰了刘管事几句,但心里却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几天后,一个浑身是血的伙计,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平安客栈。
“救……救命……”
林默立刻让人将他扶进来,又是请大夫,又是喂水。
等那伙计缓过气来,才断断续续地说,他们是一支小商队,在前面的黑风口,被一伙悍匪给劫了。货物被抢,人也被打伤了好几个。
林.. The man's description of the bandits' leader caught hisattention. A tall man with a long scar across his left eyebrow.
Lin Mo's heart sank.
He remembered this man. In his past life, after his stepmother wastaken, he had spent years trying to find her. He had heard rumors of agroup of bandits who had been active in the area at that time. Theirleader was a man with a scar on his eyebrow. Eventually, he learned thatthis group had been wiped out by the army, and all the women they hadcaptured had either been killed or sold off to distant places. He hadnever found any trace of Chen Shu. It was the biggest regret and pain ofhis life.
He hadn't expected to encounter this man again in this life.
He immediately understood that this was not just a random group ofbandits. This was a threat that could destroy everything he hadbuilt.
He couldn't just rely on the government. He had to take matters intohis own hands.
He spent a large sum of money to hire a group of skilled guards toprotect the inn. He also sent peopl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bandits.
He learned that the bandits were hiding in a complex of caves in thenearby Black Wind Mountain. The terrain was treacherous and easy todefend, which was why the government's attempts to suppress them hadfailed.
Lin Mo knew he couldn't fight them head-on. He had to use hiswits.
He remembered a detail from his past life. The bandit leader was notonly ruthless but also extremely greedy. He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arare and expensive type of northern ginseng.
An idea began to form in Lin Mo's mind.
第十六章
林默找到了刘管事。
“刘大哥,我想请您帮个忙。”
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刘管事听完,惊得目瞪口呆:“林老弟,你……你疯了?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去引蛇出洞?这太危险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林默的眼神异常坚定,“这伙悍匪不除,商道不宁,我的客栈也永无宁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所有走这条商道的人。”
他详细地分析了计划的可行性。
他会放出风声,说自己收到了一批极品的北地山参,价值连城,准备运往南方。他会亲自押送,但只带少数几个护卫,装作实力不济的样子,从黑风口经过。
而刘管事,则需要带着商队的主力,悄悄埋伏在黑风口附近。同时,林默已经派人去府城报官,请求官兵配合,形成一个包围圈。
只要悍匪头目上钩,他们就来一个瓮中捉鳖。
这个计划,风险极大。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林默都可能万劫不复。
刘管事看着林默,这个比他小了十几岁的年轻人,此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他最终一咬牙:“好!林老弟,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件事,我帮你!”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悍匪的耳朵里。
正如林默所料,那个贪婪的匪首,果然动了心。
三天后,林默带着一个装着“山参”的箱子,和四个护卫,赶着一辆马车,缓缓驶入了黑风口。
山谷里,一片寂静,只有风声和马蹄声。
但林默能感觉到,在两旁的密林中,有无数双眼睛,正像狼一样盯着他们。
当他们走到山谷最狭窄处时,意外发生了。
从天而降的一张大网,将他们连人带车,都罩在了里面。
紧接着,上百名手持兵刃的悍匪,从林中冲了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
一个身材高大、左边眉骨上有一道狰狞刀疤的男人,狞笑着走了出来。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小子,把你手里的山参,乖乖交出来!”
林默心中一沉。
情况,和他预想的有些出入。他没想到对方会用这种方式,直接将他们困住。
但他面上依旧保持着镇定。
“东西可以给你,但你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
“哈哈哈哈!”刀疤脸狂笑起来,“到了我的地盘,还想谈条件?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吗?”
他挥了挥手,几个悍匪立刻上前,就要割开网,抢夺箱子。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
只听“嗖嗖嗖”几声,几支利箭,从林中射出,精准地射倒了那几个上前的悍匪。
紧接着,四面八方传来了喊杀声。
刘管事带着商队的护卫,从一侧杀了过来。而另一侧,官兵的旗帜,也出目前了山头。
“中计了!快撤!”刀疤脸脸色大变,立刻下令。
悍匪们顿时乱作一团。
一场混战,就此展开。
林默趁乱用匕首割开大网,带着护卫冲了出来。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刀疤脸匪首!
前世的仇,今生的怨,在这一刻,尽数涌上心头。
他不会让这个人,再有机会逃脱!
第十七章
刀疤脸匪首的确 悍勇,他挥舞着一把鬼头大刀,接连砍翻了好几个官兵,企图杀出一条血路。
林默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但他没有退缩。
他从地上捡起一把朴刀,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刀疤脸的后心,狠狠地刺了过去。
他用的是前世在街头为了保护弟弟而学会的、最不入流的打架招式,没有任何章法,只有一股同归于尽的狠劲。
刀疤脸感受到了身后的杀气,猛地回身,用大刀格挡。
“当!”的一声,林默的刀被震飞,虎口鲜血淋漓。
“找死!”刀疤脸眼中凶光大盛,举刀就要砍向林默。
就在这时,一支冷箭,从斜刺里射来,正中他的手腕。
刀疤脸惨叫一声,鬼头大刀脱手落地。
一个矫健的身影,从旁边冲了出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是刘管事。
官兵和护卫们一拥而上,将刀疤脸死死地按住。
大局已定。
林默看着被捆得像粽子一样的刀疤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人都虚脱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赢了。
这场豪赌,他赢了。
第十八章
黑风口的悍匪被一网打尽,云门商道从此畅通无阻。
林默智勇双全、配合官府剿匪的事迹,也传为了一段佳话。府城的知府大人,亲自接见了他,并赏赐了一块“义勇可嘉”的牌匾。
平安客栈,彻底成了商道上的一块金字招牌。
林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他采纳了林风的提议,在刘管事的协助下,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支商队,往返于南北之间,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他开了分店,涉足了药材、丝绸、粮食等多个行业。
短短几年时间,林家,就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农户,一跃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商。
林默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他出资修路、建学堂,协助村里的乡亲改善生活。
陈淑成了受人尊敬的老夫人。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家含饴弄孙……哦不,是看着两个越来越有出息的儿子,笑得合不拢嘴。
林风也长成了一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不再需要林默的庇护,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打理着家族的大部分生意。兄弟二人,齐心协力,将家业经营得红红火火。
一切,都好得像一场梦。
但林默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结。
那个刀疤脸匪首,在被处决前,他去牢里见过他一面。
他问他,十几年前,他是否劫掠过一个叫林家村的村子,是否掳走过一个叫陈淑的女人。
刀疤脸想了很久,才咧着嘴,露出一口黄牙,说:“抓的女人太多了,记不清了。不过,我们抓来的女人,要么兄弟们自己分了,要么……就卖给了南边过来的人牙子。”
人牙子……
这个线索,让林默的心,再次沉了下去。
他知道,那个前世让他悔恨一生的人,或许,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某个角落。
第十九章
林默开始不惜代价地寻找陈淑。
他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财力,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南方各地打探消息。
但人海茫茫,要找一个十几年前被卖掉的女人,何其艰难。
一年,两年,三年……
时间一天天过去,传回来的,都是失望的消息。
就连林风和陈淑(这个世界的陈淑,林默已经习惯叫她娘),都劝他放弃。
“哥,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许……也许人已经不在了。”
“阿默,别找了。目前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林默没有说话。
他知道他们说得有道理。
但他无法放弃。
这是他重活一世,最大的执念。
如果找不到她,他这一生,终究是不完整的。
这天,他派去南方的人,终于带回来一个消息。
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姓陈的妇人,十几年前被人从北方买来,嫁给了一个体弱多病的秀才。秀才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她没有再嫁,而是独自一人,靠着给人洗衣、做绣活,拉扯着秀才留下的一儿一女。
所有的信息,都和林默要找的人,有几分类似。
林默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交代好家里的事情,带着几个亲信,踏上了南下的路。
第二十章
江南小镇,烟雨朦胧。
林默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户人家。
那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墙上爬满了青苔。
他推开虚掩的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衫的妇人,正坐在廊下,低头做着针线活。她的身边,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在认真地描红。
妇人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脸上也刻上了岁月的风霜,但那温婉的眉眼,依稀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林默的脚步,停住了。
他看着那个身影,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似乎是听到了脚步声,那妇人抬起头。
当她看到林默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手里的针线,掉在了地上。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阿默?”她试探着,用一种不确定的、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声音,轻轻地喊了一声。
林默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快步走上前,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她的面前。
“娘!”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这个迟到了两世的称呼。
“我来接您回家了。”
(完)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