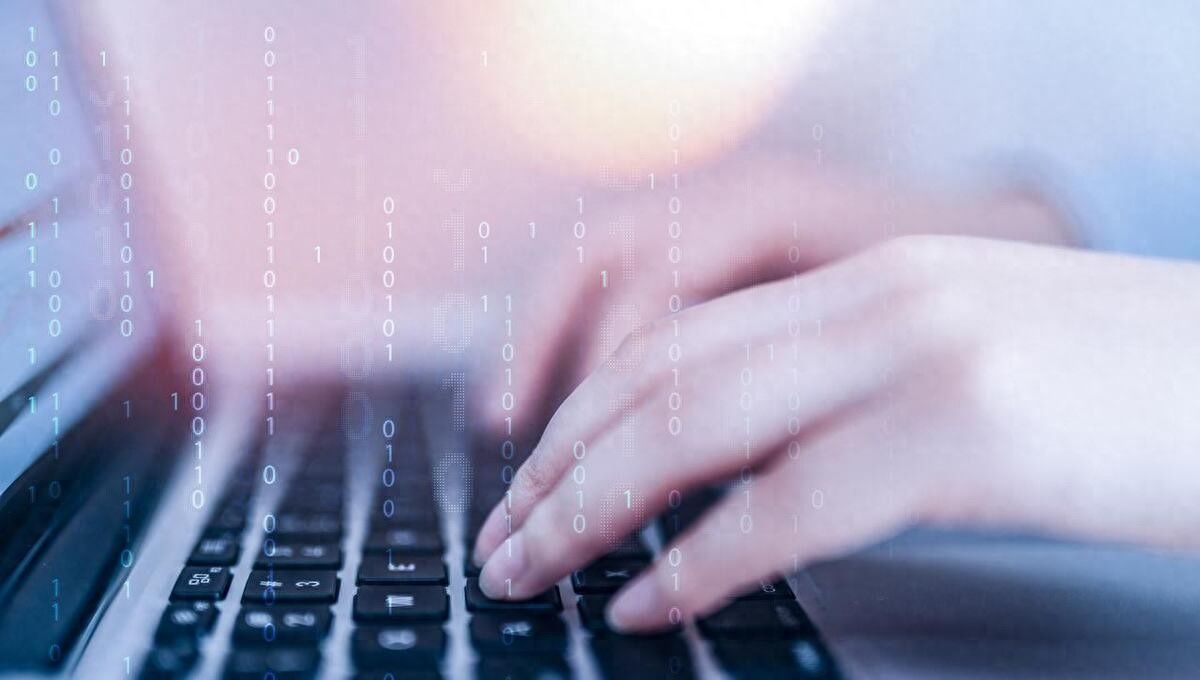可别小瞧那只掉了漆的旧算盘,它差点没把我们家的日子搅翻了天!
1952 年的秋末,风已经带着凉劲儿了,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村东头老槐树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就剩几根光秃秃的枝桠挑着天。我当时正蹲在院门口啃红薯,红薯是前几天从地里挖的,皮上还带着泥,咬一口甜得流蜜,嘴里的红薯渣刚要往下咽,就听见村西头传来大嗓门 —— 是村长张大叔的声音,他嗓门亮,不用喊远,半个村都能听见。
“老实!老实在家没?”
我爹王老实正在院里编竹筐,手里拿着竹子劈的细条,听见喊声,手顿了顿,抬头往门口瞅:“在呢!张哥啥事儿?”
张大叔扛着个长东西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民兵,一个扛着小方桌,一个抱着两把椅子,裤腿上都沾着泥,看样子是刚从地主家那边过来。我们村的地主姓刘,前阵子土改,他家的地和东西都要分下去,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分点,我娘前几天还跟我爹念叨,说要是能分个锅就好了,家里那口老锅补了好几次,都快漏了。
张大叔把扛着的东西往地上一放,我才看清是个算盘,长溜溜的,木头框子是深棕色的,掉了不少漆,露出里面浅黄色的木头,算珠是黑褐色的,有三个珠子裂了缝,用细绳子绑着,还有一个珠子颜色浅点,看着像是后来配的。
“老实,这是你家分的,” 张大叔抹了把脸上的汗,虽说天凉,他还是跑得出了汗,“刘地主家的东西,这算盘虽说旧了,珠子还能动,后来给狗蛋(我小名)算账用得着,他不是明年要去镇上上学了吗?”
我爹赶紧放下手里的竹条,走过去接算盘,手指刚碰到木头框子,就 “嘶” 了一声 —— 那木头凉得渗手。他把算盘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嘴角带着点笑:“这东西金贵啊,以前只在刘地主家见过,他当年算账的时候,就靠这玩意儿,噼啪响。”
我娘李氏正攥着针线在屋里补我的破裤子,听见外面的动静,赶紧放下针线迎出来,手里还拿着顶没缝好的布帽子。她看见算盘,眼睛亮了亮:“张哥,这算盘真是给我们家的?能有这东西,后来狗蛋上学,算术肯定能学好。”
张大叔笑了:“可不是嘛,按人头分的,你们家三口人,除了这算盘,还有张桌子两把椅子,都在后面呢,等会儿让民兵帮你们搬屋里去。”
我妹丫蛋当时才 8 岁,正趴在地上玩泥巴,手里捏着个小泥人,看见张大叔他们扛着东西来,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仰着小脸问:“张大叔,这长木头是啥呀?能玩吗?”
张大叔蹲下来,摸了摸丫蛋的头,指了指算盘上的珠子:“这叫算盘,能算账,也能玩,你拨拨看,珠子能滑来滑去。”
丫蛋伸手就去拨珠子,“啪嗒” 一声,珠子撞到框子上,她吓得赶紧缩回手,然后又咯咯笑起来:“好玩!比我的泥人好玩!”
我也凑过去,想摸摸算盘,我爹把我扒拉到一边:“别瞎碰,这东西脆,别给碰坏了。” 他说着,就把算盘抱起来,往屋里走,我娘赶紧跟在后面,嘴里念叨着:“放哪儿好呢?放堂屋的桌子上吧,显眼,也不容易碰着。”
民兵把桌子和椅子搬进屋,张大叔又跟我爹聊了几句,说后来要是有啥困难就找他,然后就带着民兵去下一家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娘赶紧把屋门关上,生怕风把算盘吹着似的,我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把算盘放在腿上,开始拨弄起来。
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个算珠,轻轻一拨,“啪嗒” 一声,珠子就从一边滑到另一边,他先是从右往左拨,嘴里还念叨着:“一亩地收三担玉米,五亩地就是十五担,除去种子和肥料,能剩十三担……”
我娘站在旁边看着,手里还拿着那顶布帽子,缝着缝着就忘了走线:“他爹,你以前给刘地主当长工时,是不是天天看他用这算盘?”
我爹点点头,拨珠子的手没停:“可不是嘛,我 20 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就去给刘地主当长工,天天跟着他下地,到了月底算账,他就把这算盘拿出来,噼啪噼啪算,算错一点就瞪眼睛,有一次我给他报收成,多报了半担,他用这算盘一算,发现不对,拿起烟袋锅子就往我胳膊上敲,疼了好几天。”
丫蛋坐在我爹旁边的小凳子上,伸手想去拨珠子,我爹把她的手拦住:“慢点儿,别把珠子弄掉了,这珠子掉了可不好配。” 他说着,手指碰到了算盘底框的一道划痕 —— 那划痕挺深的,像是被斧头砍过似的,我爹的手突然顿住了。
一开始我还没在意,以为他就是累了,可接着,我就看见他脸上的笑慢慢没了,嘴角往下耷拉着,脸色一点点变白,手也开始抖,连带着腿上的算盘都跟着晃,算珠 “哗啦啦” 响个不停。
我娘也看出不对劲了,停下手里的针线,走过去问:“他爹,咋了?手咋抖成这样?是不是冷了?”
我爹没说话,眼睛死死盯着算盘的底框,手指在那道划痕上摸来摸去,然后突然把算盘翻了过来,底朝天放在腿上,用指甲抠着底框的缝隙,像是在找啥东西。他的指甲缝里还沾着编竹筐时的竹屑,抠得指节都发白了。
“你倒是说话啊,咋了这是?” 我娘又问了一句,声音里带着点慌。
我爹这才抬起头,声音有点哑,还带着点颤:“你们…… 你们别过来,离远点。”
我和丫蛋都愣了,丫蛋刚要站起来,就被我娘拉住了。我娘皱着眉:“你这是咋了?好好的发啥脾气?不就是个算盘吗?有啥不能看的?”
我爹没理我娘,继续用指甲抠算盘的底框,突然 “咔嗒” 一声,底框的一块木头居然被他抠开了,露出一个小缝,里面好像有啥东西闪了一下。他赶紧把手指伸进去,抠出来一小块圆溜溜的东西,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
我凑过去看,那圆溜溜的东西是银白色的,上面还有花纹,我娘 “呀” 了一声:“这是…… 这是银圆吧?”
我爹没说话,把银圆攥在手里,又展开那张纸条,纸条是黄颜色的,上面用毛笔写着字,我那时候才 12 岁,只认识几个字,看见上面有 “刘”“粮”“西” 几个字,其他的都不认识。
我爹看完纸条,脸色更白了,手都开始发颤,把银圆和纸条紧紧攥在手里,像是怕被人抢了似的。他猛地站起来,把算盘往我怀里一塞,声音急促地说:“狗蛋!快!拿着这算盘,去村东的河里扔了!扔远点儿!别让任何人看见!”
我被他推得一个趔趄,赶紧抱住算盘,算盘沉得很,硌得我胳膊生疼。我愣了愣,说:“爹,这算盘能算账,扔了多可惜啊?再说这银圆,交上去说不定还能换点钱呢,咱们家不是还缺个锅吗?”
“让你扔你就扔!别问那么多!” 我爹急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吓得丫蛋往后缩了缩,眼圈都红了。
我娘赶紧扶住我,对我爹说:“他爹,你干啥呀?娃说得对,银圆交公,算盘留着,扔了多可惜?这可是分咱们家的东西,又不是偷的抢的,怕啥?”
“你懂啥!” 我爹瞪着我娘,眼睛里都是慌,“这算盘是刘地主家的!他藏东西的本事大着呢,谁知道这里面还有啥?要是被民兵知道了,说咱们私藏地主财产,那可是要被批斗的!我当年给刘地主当长工时,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他肯定在这算盘里藏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咱们家要是留着这算盘,早晚要出事!”
我娘还是不乐意:“目前是新社会了,分的东西就是咱们的,就算里面有银圆,交上去不就完了?民兵也不会不讲理啊,张大叔不是说了吗,有困难找他,咱们跟他说说,肯定没事。”
“不行!” 我爹斩钉截铁地说,“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刘地主目前被关起来了,他儿子还在外面跑,要是知道这算盘在咱们家,说不定会来找麻烦!快,狗蛋,赶紧去扔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丫蛋拉着我爹的衣角,小声说:“爹,我还想玩算盘呢,别扔好不好?”
我爹低头看着丫蛋,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还是皱着眉:“丫蛋乖,后来爹给你做个木头的,比这个好玩,这个不能留,听话。”
我还是不想扔,这算盘多好啊,后来上学能用上,再说扔到河里多可惜。我站着没动,我爹又要推我,我娘赶紧拦住他:“他爹,你别逼娃了,要不咱们先把算盘藏起来,等明天问问张大叔,要是没事再留着,要是有事再扔也不迟啊。”
我爹想了想,脸色还是不好看,但还是点了点头:“行,先藏起来,别让任何人看见。狗蛋,你把算盘抱进里屋,塞到床底下的箱子里,用衣服盖严实了。”
我赶紧抱着算盘进了里屋,里屋是我和爹睡的地方,床底下有个旧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我把衣服扒拉到一边,把算盘塞进去,又用衣服盖好,拍了拍,确定看不见了,才走出去。
我爹还坐在椅子上,手里攥着银圆和纸条,脸色还是发白。我娘给他倒了碗热水,说:“喝点水吧,别吓着自己了,咱们没做亏心事,不怕啥。”
我爹接过碗,喝了一口,手还是在抖:“我不是怕别的,是怕再回到以前的日子。当年给刘地主当长工,天天累死累活,还吃不饱饭,有时候算错一点账,就被他打骂,目前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地,有了自己的家,我不想再出事。”
我娘叹了口气:“我知道你苦,可目前不一样了,有政府,有民兵,没人敢欺负咱们了。那银圆和纸条,明天咱们交给张大叔,让他处理,这样就没事了。”
我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把银圆和纸条揣进怀里,然后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和丫蛋坐在炕沿上,也不敢说话,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刮着窗户纸,“呼呼” 响。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爹就起来了,他没去下地,而是坐在堂屋里抽烟袋,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杆里的烟丝都快烧完了。我娘起来做饭,熬了点玉米粥,蒸了几个红薯,喊我们吃饭,我爹也没动。
“吃点吧,不吃东西咋行?” 我娘把粥端到他面前,“今天咱们去问问张大叔,把银圆和纸条交给他,心里就踏实了。”
我爹这才端起碗,喝了一口粥,没吃红薯。吃完饭,我爹揣着银圆和纸条,就要去找张大叔,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张大叔带着两个民兵往我们家来,我爹的脸一下子又白了,赶紧把怀里的东西往我娘手里塞:“快,藏起来!”
我娘赶紧把银圆和纸条塞到围裙口袋里,然后迎出去:“张哥,咋这么早过来了?有事吗?”
张大叔笑着说:“没啥大事,就是昨天分东西,怕你们家搬不动,过来看看。对了,昨天分的算盘,你们用着还行?”
我爹站在后面,声音有点不自然:“还行…… 还行,就是有点旧了,暂时用不上。”
张大叔没在意,走进屋看了看,说:“这桌子椅子放得挺合适,后来你们家吃饭、写字都方便了。对了,昨天区里来了通知,说刘地主的儿子回来了,到处找他家以前藏的东西,你们要是看见啥可疑的人,或者发现啥可疑的东西,赶紧跟我说。”
我爹赶紧点头:“知道了张哥,我们要是看见,肯定跟你说。”
张大叔又聊了几句,就带着民兵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爹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还好没问起算盘,咱们目前就去交银圆和纸条,省得夜长梦多。”
我娘拿出银圆和纸条,跟着我爹一起去找张大叔。我和丫蛋在家等着,心里有点慌,怕出事。过了大致一个时辰,我爹和我娘回来了,我爹的脸色比早上好多了,手里还拿着算盘 —— 原来他们把算盘也抱去了,跟张大叔说了事情的经过。
我赶紧问:“爹,没事了吧?”
我爹笑了笑,把算盘放在桌子上:“没事了,张大叔说,目前是新社会,不用怕刘地主,这银圆交公,纸条是刘地主借了邻村王大爷的钱,已经还给王大爷了,这算盘还是咱们家的,后来留着用。”
我娘也笑着说:“张大叔还说,后来有啥不懂的,就问他,别自己吓自己。”
丫蛋一听算盘还是咱们家的,赶紧跑过去拨珠子,“啪嗒啪嗒” 响,笑得特别开心:“我就知道不用扔,这算盘最好玩了!”
我爹看着丫蛋,也笑了,他拿起算盘,用布擦了擦上面的灰,又找了点砂纸,把掉漆的地方磨了磨,然后从屋里找出一点红漆,是以前刷家具剩下的,他用小刷子蘸着漆,把裂了缝的珠子补了补,又在掉漆的地方刷了点漆,虽然刷得不太均匀,但看着比以前好看多了。
从那后来,这算盘就成了我们家的宝贝。我每天放学回来,就坐在桌子前,用它算算术,我爹有时候也会教我怎么用算盘算账,他说:“这算盘讲究个指法,食指管下面的珠子,中指管上面的,拨的时候要快,还要准,这样算得才快。”
我娘有时候会把算盘拿过去,算家里的开销,列如买了多少米,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她算得慢,但每次算完都会笑:“有这算盘就是好,再也不用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得也准。”
冬天的时候,天特别冷,下了好几场雪,村里的路都被雪盖住了,我爹不用下地,就在家里编竹筐,编完了就用算盘算卖竹筐能换多少钱,他说:“一个竹筐能卖两毛钱,编十个就是两块钱,够给你们买过年的新衣服了。”
丫蛋那时候已经会算 100 以内的加减法了,她常常拿着算盘,坐在炕上学算术,有时候算错了,就噘着嘴问我:“哥,二加三等于几啊?我咋算不对呢?”
我就教她:“下面一个珠子代表一,上面一个代表五,二加三,就拨两个下珠,再拨三个下珠,加起来就是五个,对吧?”
丫蛋点点头,又拨了一遍,算对了,就高兴得拍手:“我会了!我会了!”
过年的时候,家里特别热闹,我娘蒸了好多馒头,还买了两斤猪肉,包了饺子。我爹用算盘算着年货的钱,说:“买猪肉花了一块五,买糖果花了五毛钱,买红纸花了一毛钱,总共花了两块一,还剩五块九,明年春天给狗蛋交学费够了。”
我娘笑着说:“够了够了,学费才三块钱,还能剩点给娃买支新笔。”
大年初一那天,我穿着新衣服,拿着算盘去给张大叔拜年,张大叔看见算盘,笑着说:“这算盘还挺好的,没白留着吧?”
我说:“嗯,我目前算算术可快了,老师都夸我呢!”
张大叔摸了摸我的头:“好好学,后来用这算盘算更多的账,为咱们村做贡献。”
后来我 15 岁的时候,去县城上中学,我爹把算盘用布包好,塞到我的行李里,说:“带着吧,在学校算算术用得着,这算盘跟着咱们家这么多年了,是个好东西。”
我娘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还在布包里放了个小布片,说:“要是算盘坏了,就用这布片擦擦,别让它生锈了。”
到了学校,老师看见我的算盘,特别高兴,说:“目前学校里虽然有算术课本,但用算盘算账还是很重大的,你有这算盘,后来学算术肯定能学好。”
我在学校里,每天都用算盘算算术,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个老算盘,有时候他们会借我的算盘用,我都会借给他们,还教他们怎么用。
放假回家的时候,我爹早早就到村口等我,他看见我回来,赶紧接过我的行李,第一句话就是:“算盘没坏吧?在学校用着还行?”
我说:“没坏,用着挺好的,老师还夸我算得快呢!”
我爹听了,笑得特别开心,他接过算盘,打开布包看了看,说:“没坏就好,没坏就好。”
我娘做了我最爱吃的鸡蛋面,里面卧了两个鸡蛋,说:“在学校肯定没吃好,回来多补补。”
丫蛋那时候已经 11 岁了,上小学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哥,我目前会用算盘算乘法了,你考考我!”
我笑着说:“好啊,三乘四等于几?”
丫蛋赶紧拿起算盘,拨了几下,说:“等于十二!”
我点点头:“对了,真厉害!”
丫蛋高兴得蹦了起来:“我就知道我能算对!”
后来我参与工作了,在县城的供销社当会计,每天都要用算盘算账,同事们都说我算得又快又准,我说:“都是我爹教我的,还有这只老算盘的功劳,它跟着我这么多年了,算得特别准。”
工作几年后,我把父母和妹妹都接到了县城,那只算盘也带了过去,我把它放在客厅的柜子上,我娘没事的时候就会擦一擦,掉漆的地方她用红漆补了又补,虽然补得不太好看,但看着特别亲切。
我爹退休后,每天早上都会拨弄一会儿算盘,他说:“这声音听着就舒服,比收音机还好听,想起以前在村里的日子,就觉得目前的日子真好。”
目前我也有了儿子,儿子小时候常常拿着算盘玩,他问我:“爸,这是什么呀?怎么跟计算器不一样?”
我说:“这叫算盘,是以前算账用的,比计算器老多了,是你爷爷当年从地主家分来的,跟着咱们家几十年了。”
儿子好奇地拨着算珠,说:“真有意思,我也要学用算盘算账!”
我爹就会教他,像当年教我一样,说:“这算盘讲究个指法,食指管下面的珠子,中指管上面的……”
每次看到那只掉了漆的旧算盘,我就想起 1952 年的那个秋末,想起我爹当时发白的脸,想起我娘的担忧,想起丫蛋的哭闹,想起张大叔的帮忙。它就像一个老朋友,陪着我们家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我们家的好日子,也见证了新社会的好光景。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