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你听。
那不是风声,也不是水声。那是一种穿越了九千年时光的呼吸,从河南贾湖一根小小的兽骨里,悠悠地吹了出来。
它只有一个名字,叫骨笛。

有人用它吹响了《小白菜》的旋律,音阶完整,清亮得不像话。九千年前,当世界上大多数人还在为下一顿果腹而奔波时,我们的祖先,居然已经开始用音乐,与天地对话。
这声音里,藏着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秘密。一个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最深层的答案。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了一个数字:五千年。甚至,有人更苛刻,拿着一把来自古巴比伦的尺子,量了量我们的历史,说,不好意思,从甲骨文算起,顶多3300年。
仿佛我们悠远的历史,都得先得到他们的点头承认,才能算数。
这事儿,挺憋屈的。
但那根骨笛不这么认为。它在地下沉睡了九千年,一出土,就用它的声音,轻轻地,却又不容置疑地告知世界:你们看的,是文字;而我们玩的,是秩序。

你看,贾湖的墓葬里,有的人身边堆满了玉器和陶器,而有的人,却孤零零地躺着,身无长物。这不是偶然,这是阶级。有了阶级,就有了分工,有了管理。
而那支骨笛,往往出目前最“富有”的墓主身边。它不是玩具,它是权力的号角,是祭祀的通天之梯。
当一群人开始用固定的音律来表达敬畏,来划分等级,这本身,就是一种比文字更古老的“文明语法”。
它在说,我们早就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了。
这幽幽的笛声,像是投入历史深湖的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将我们带向了更遥远的过去。
是什么,供养了这群有闲情逸致制造乐器、建立秩序的人?
答案,在一粒米里。

时间再往前拨九千年,我们来到一万八千年前的湖南,玉蟾岩。那里的山洞里,藏着几粒烧焦的稻谷。起初没人觉得稀奇,直到碳14测定的结果出来,所有人都沉默了。
一万八千年。
那不是野生的,是人工栽培的。我们的老祖宗,在冰河时代末期,就已经懂得从万千植物中,筛选、培育出能填饱肚子的主食。
他们弯下腰,在泥泞里筛选种子的那一刻,文明的火种,就已经被点燃了。那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那只是为了让家人,能吃上一口更香的饭。
这最朴素的愿望,却成了我们这个文明最坚韧的底色。

从一万八千年前的稻谷,到一万年前浙江上山,成片成片的规整稻田,沟渠纵横,俨然一派江南水乡的雏形。有了稳定的食物,人们才能停下迁徙的脚步,才能仰望星空,才能去思考,音乐和美。
那从贾湖骨笛里飘出的旋律,它的根,就深植在这一万八千年的稻田里。笛声里,有米饭的香气。
而故事,还远未到高潮。
如果说,一粒米是生存,一支笛是精神,那么,一座城,就是野心。

将时间的指针拨到五千三百年前,杭州良渚。一座巨大的古城拔地而起。
西方学者一开始是撇嘴的。他们说,没有青铜器,没有文字,你们这顶多算个大型部落聚落。
可他们不懂,良渚人把所有的智慧,都倾注在了更宏大的事业上——治水。
他们修建了一套庞杂到令人发指的水利系统,外围水坝绵延几十公里,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工程量超过一千万立方米,比古埃及的任何水渠都更宏伟。
为了筑堤,他们用竹筐装满泥土,一块一块地垒。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成千上万的人,在统一的号令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日复一日地劳作。
这不叫国家,什么叫国家?

当你站在良渚古城的遗址上,你听到的,就不再是骨笛的独奏了。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呐喊,是泥土被夯实的闷响,是水流被驯服的轰鸣。
这是一首由整个社会合奏的,名为“国家”的交响乐。
而统一的玉器信仰,就是这首交响乐的指挥棒。从东北的红山,到江南的良渚,类似的玉龙、玉琮,穿越千山万水,诉说着一个共同的信仰。
我们早就开始用一种超越血缘的文化,将彼此凝聚在一起了。
目前,我们再回头看那把“西方标准”的尺子。“文字、青铜、城市”,这三样东西,更像是为尼罗河和两河流域的文明“量身定做”的一套西装。
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礼服。我们的礼服,是用稻谷的纤维织成的,用骨笛的音律染色的,用美玉的光泽点缀的。凭什么要脱下自己的衣服,去硬套别人的尺寸?
【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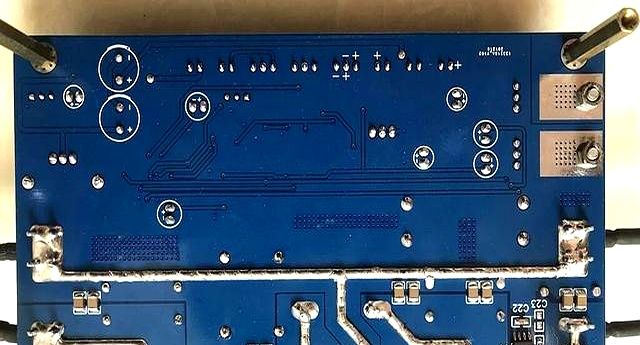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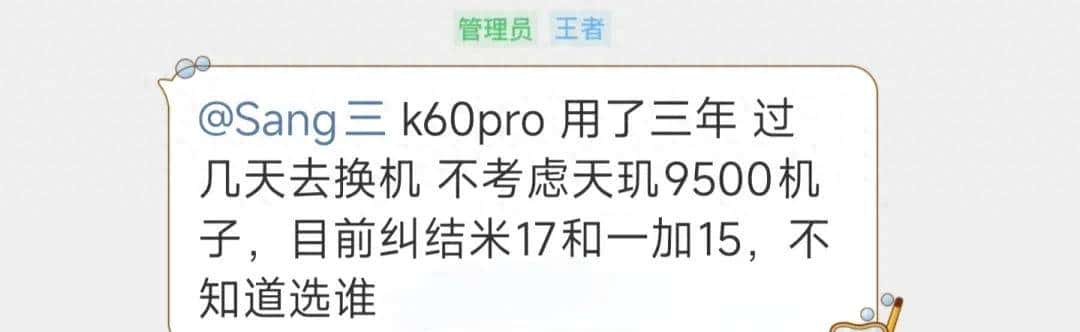


文化与哲学的区别,以骨笛为例:将长骨吹响是一种民族文化;在长骨上打响划分等级以固定音律是哲学、哲学归属人类,哲学是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