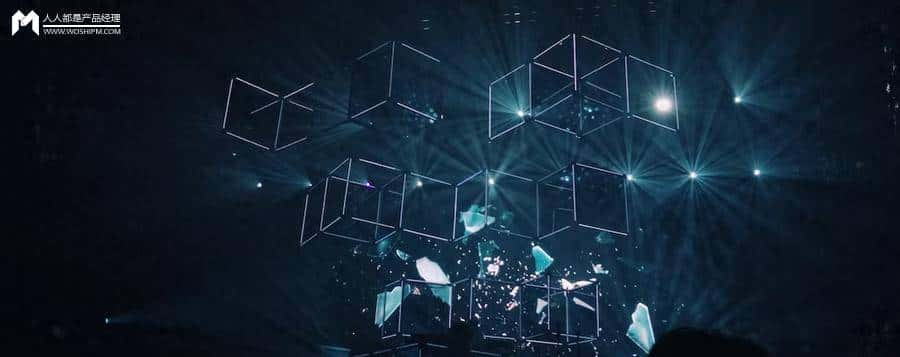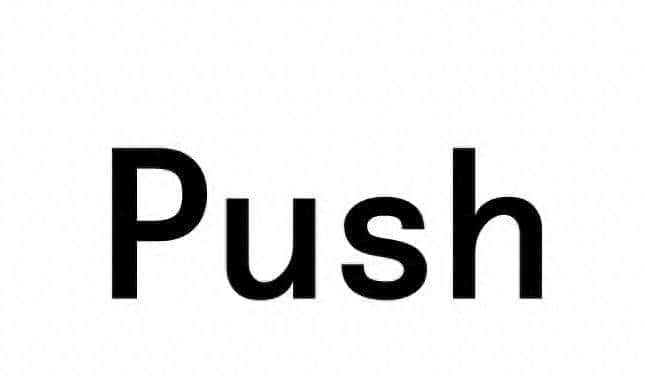72年修水库,一个成分不好的女人为了给我送饭,摔伤了脚
在苏婉清孙子的婚礼上,我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把一个房本和一把车钥匙,轻轻推到了那对新人面前。司仪当场就懵了,话筒拿在手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新郎新娘更是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连连摆手说:“石伯伯,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万万不能要!”
我的儿子儿媳也急了,在底下拼命拉我的衣角,压着嗓子说:“爸,您这是干什么?这礼也太重了!”
我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稍安勿躁。我拿起话筒,看着台下一张张惊愕的脸,声音有些发沉,但很稳:“孩子们,收下吧。这点东西,跟我石卫东欠你们奶奶的相比,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五十年前,要不是她那一碗饭,一个崴了的脚脖子,这世上,早就没有我石卫东了。”

这话一出,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地一下,聚焦到了坐在主桌,那个头发花白、腿脚有些不便的清瘦老人——苏婉清身上。而这一切,都要从1972年,那个尘土飞扬的冬天说起。
那年我刚满十八,是个热血上头、浑身使不完劲儿的愣头青。响应号召,我们整个公社的青壮劳力都去了几十里外的卧龙山,修水库。那是个苦差事,天不亮就得上工,天黑透了才收工。住的是临时搭的工棚,四面漏风。吃的更是差,一天三顿高粱米饭配一勺盐水煮白菜,清汤寡水,一点油星子都见不着。
年轻人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那点伙食根本不够填肚子的。每天累得像条死狗,晚上躺在通铺上,饿得前胸贴后背,听着周围一片磨牙和说梦话的声音,心里就一个念头:想吃一顿饱饭,最好是白面馒头,哪怕是粗粮做的窝窝头也行。

工地上干活的人,成分复杂。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自然是主力军,干活最卖力,口号也喊得最响。而另一拨人,就是像苏婉清那样的,被划为“成分不好”的,专门负责一些最脏最累的杂活,列如清理厕所、挑运土方。
苏婉清那时候也就三十出头,但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她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头发也总是乱糟糟的。听说她家以前是地主,她父亲还是个读过书的“臭老九”,早些年就被批斗死了。她丈夫受不了牵连,跟她划清界限离了婚,就剩她一个人带着个几岁的儿子,日子过得针扎一样。

在那个年代,“成分”就像一个烙印,死死地刻在人身上。我们这些热血青年,被教育得要“阶级立场坚定”,见了他们这种人,都恨不得绕道走,生怕沾上一点“不清白”。工地上,大家都不跟她说话,领头的马刚队长更是把她当成了反面教材,动不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呵斥她“思想落后”、“改造不积极”。她从不辩解,只是默默地把头埋得更低。
可我总觉得,她和别人嘴里说的“坏分子”不太一样。她的眼睛很干净,像一潭秋水,虽然总是躲闪着,但偶尔抬眼的一瞬间,你能看到一种不属于这里的温柔和澄澈。她干活很仔细,哪怕是打扫我们那臭气熏天的工棚厕所,也弄得比别处干净。只是,没人会夸她,只会觉得这是她“赎罪”该做的。
那天,改变了我一生的事情发生了。前一天晚上,由于一件小事,我跟隔壁村的二愣子打了一架。马刚队长为了“严肃纪律”,罚我们俩不准吃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还要做双倍的工。

那滋味,真是生不如死。本来就饿,再扛着一天一夜不吃饭,还得在寒风里挖土方,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在了一起,眼前直冒金星。到了第二天晌午,别人都去食堂吃饭了,工地上只剩下我和二愣子,还有零星几个像苏婉清一样干杂活的人。
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感觉连呼吸都费劲。胃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咬,火辣辣地疼。我当时就想,怕不是要死在这卧龙山了。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小伙子……你……你把这个吃了吧。”

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到苏婉清站在我面前,手里捧着用一块蓝布手帕包着的东西,手帕上还带着补丁。她满脸都是紧张和不安,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我愣住了。那年月,谁家的粮食不是命根子?更何况是她这种连生存都艰难的人。她打开手帕,里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玉米面窝窝头,和一个咸鸭蛋。那金黄的窝窝头,在我眼里简直比金元宝还晃眼。
我本能地想拒绝。跟一个“成分不好”的人扯上关系,要是被马队长看见,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可肚子的“咕咕”声和那窝窝头的香气,却在疯狂地摧毁我的理智。

“婶子……我……我不能要。”我挣扎着说,声音干涩。
“快吃吧,孩子。”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恳求,“我看你脸色发白,再不吃东西要出事的。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当妈的看不了这个。”她把东西硬塞到我手里,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还有点热水,喝口暖暖身子。”

那一刻,我所有的防备和所谓的“阶级立场”都崩溃了。我抓起窝窝头,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那窝窝头虽然剌嗓子,但在我吃来,却是天底下最香甜的美味。那个咸鸭蛋,我甚至舍不得一口吃完,一小口一小口地咂摸着滋味。
苏婉清看着我吃,脸上露出了一丝极淡的微笑,像冬日里微弱的阳光。她没再多说一句话,转身就走。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那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巨大的震撼。在这个人人自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疯狂年代,竟然还有一个“坏人”,愿意冒着风险,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份恩情,我还没来得及消化,灾难就来了。

从工地回她住的那个破败牛棚,要经过一段陡峭泥泞的下坡路。前几天刚下了雪,路面结了薄冰,又滑又难走。她给我送完饭,急着赶回去,可能也是怕被人看见。就在那段下坡路上,她脚下一滑,我只听到一声短促的惊呼,她整个人就滚了下去。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扔下还没喝完的水壶就冲了过去。我跑到坡下,看到她痛苦地蜷缩在地上,抱着自己的右脚,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都咬白了。

“婶子!婶子你怎么样?”我慌了神,蹲下去想扶她。
她的右脚踝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迅速地肿了起来,像个紫色的馒头。她疼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眼睛里全是泪水,但更多的是惊恐。她指了指工地的方向,意思是让我赶紧走,别管她。
我知道她在怕什么。如果我跟她一起出现,被人看到,我就彻底说不清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接受一个“坏分子”的食物,还跟她搅在一起,我的下场可能比她还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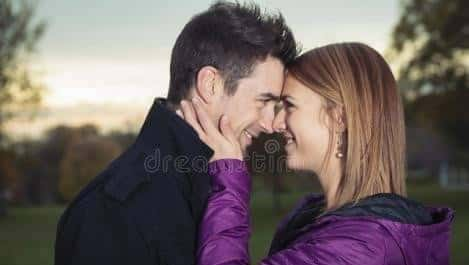
那一瞬间,我犹豫了。真的,我承认我害怕了。马刚队长那张铁青的脸,工友们鄙夷的眼神,还有可能被送回去接受“再教育”的恐惧……这些东西像无数只手,死死地拽住我的脚。
可我一低头,就看到了她那张因剧痛而扭曲的脸,还有她怀里紧紧护着的一个空了的饭盒——那是她儿子的,她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给了我。我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人不能当畜生!”我心里对自己吼了一声。我石卫东要是就这么走了,我一辈子都瞧不起自己!
我一咬牙,脱下自己身上那件还算厚实的棉袄,披在她身上。然后背起她,一步一步往山上的医务室挪。她很瘦,但对于一个饿了一天一夜的半大小子来说,依然重如泰山。那段上坡路,我走得比红军长征还艰难。每一步,脚下的冰都咯吱作响,我的腿肚子直打颤,汗水混着泪水,糊了我一脸。

我背着她出目前医务室门口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马刚队长正好也在,他一看这情景,脸立刻就黑了下来,指着我吼道:“石卫东!你干什么!你竟然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我把苏婉清轻轻放下,抹了把脸,梗着脖子说:“马队长,她为了给我送饭,摔断了脚!不管她是什么成分,她目前是伤员!”
“给你送饭?”马刚冷笑一声,“她一个地主婆,能安什么好心?我看就是想腐蚀我们革命队伍的青年!石卫东,你立场太不坚定了!这件事,要严肃处理!”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我被关了禁闭,写了几万字的检讨,每天都要在全体社员面前“深刻反省”。而苏婉清,她的脚踝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正规治疗,只是被卫生员用草药糊弄了一下,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她走路开始一瘸一拐,那条本就难走的人生路,对她来说,更加崎岖了。
水库修完后,我回了村。那件事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有好几年都抬不起头。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点都不后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晌午,那个金黄的窝窝头,和那个女人干净又带着惊恐的眼神。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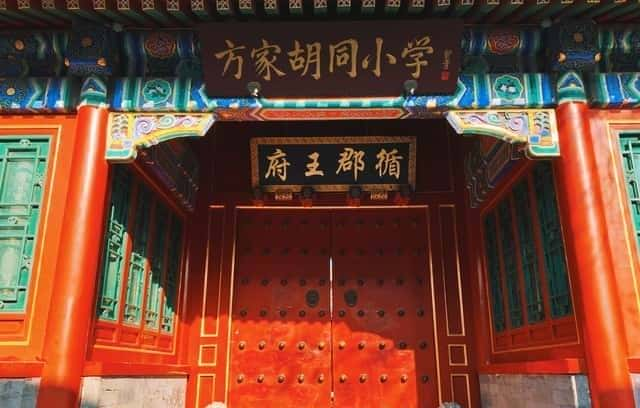
后来,时代变了。我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南下打工,吃尽了苦头,也抓住了机遇,办起了自己的小工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后来又成了市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我把父母接到城里,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
但我心里,始终有块地方是空的。那个瘸着腿的、清瘦的背影,像一根针,时常会扎我一下。

我托人打听过苏婉清的消息。听说她儿子苏建华很有出息,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她就跟着儿子,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我曾几次想去看看她,但又怕自己的出现会勾起那些不好的回忆,让她难堪。那份沉甸甸的恩情,我不知道该如何偿还。直接给钱?我觉得那是对她那份纯粹善意的侮辱。
直到去年,我从老乡口中得知,苏婉清的孙子要结婚了,但女方家要求在城里有套婚房,这可愁坏了当了一辈子老师、清贫正直的苏建华。我一听,心里豁然开朗。我知道,我报恩的机会来了。
我没有直接联系他们,而是悄悄地以一个远方亲戚的名义,用全款在他们儿子工作单位附近,买下了一套三居室,又配了一辆代步车。我知道,如果我直接给,他们家那样的风骨,是绝对不会要的。只有在婚礼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一种不容拒绝的方式送出去,他们才可能收下。我是在报恩,不是在施舍。

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在我讲完那段往事后,整个婚宴大厅鸦雀无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脸上都是无法理解的表情。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窝窝头、一个咸鸭蛋,在五十年前,意味着什么。
苏婉清在儿子苏建华的搀扶下,缓缓地站了起来。她的眼眶红了,浑浊的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滑落。她瘸着腿,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她走到我面前,没有去碰那个房本,而是伸出干枯的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就像当年看着我狼吞虎咽时一样。她的嘴唇翕动着,带着浓重的乡音,一字一句地说:“卫东……你……你是个好孩子……婶子没白疼你……”
我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商场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那一刻,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再也控制不住。我握住她冰凉的手,哽咽着说:“婶子,是我该谢谢您。要不是您,我早就饿死在卧龙山了。您那一脚,是我欠了您半辈子的债啊!”

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的儿子儿媳,也终于清楚了什么,眼圈都红了。
那一天,我心里的那块空了五十年的地方,终于被填满了。我给的不是一套房子,一辆车,我是在努力偿还半个世纪前,在一个最坏的年代里,我所收获到的,最纯粹、最宝贵的人性光辉。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许多人。锦上添花的不少,雪中送炭的难求。有的人,你一辈子都得记着,记着他在你快要冻死的时候,给你披过一件衣;记着他在你快要饿死的时候,分给你半个馍。这份恩情,比金子还贵重。你们说,对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