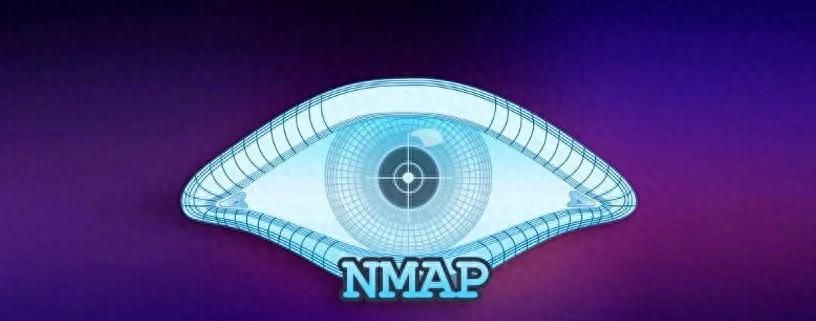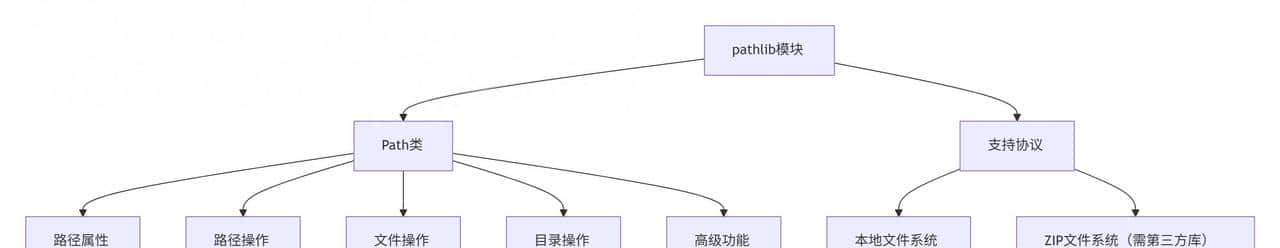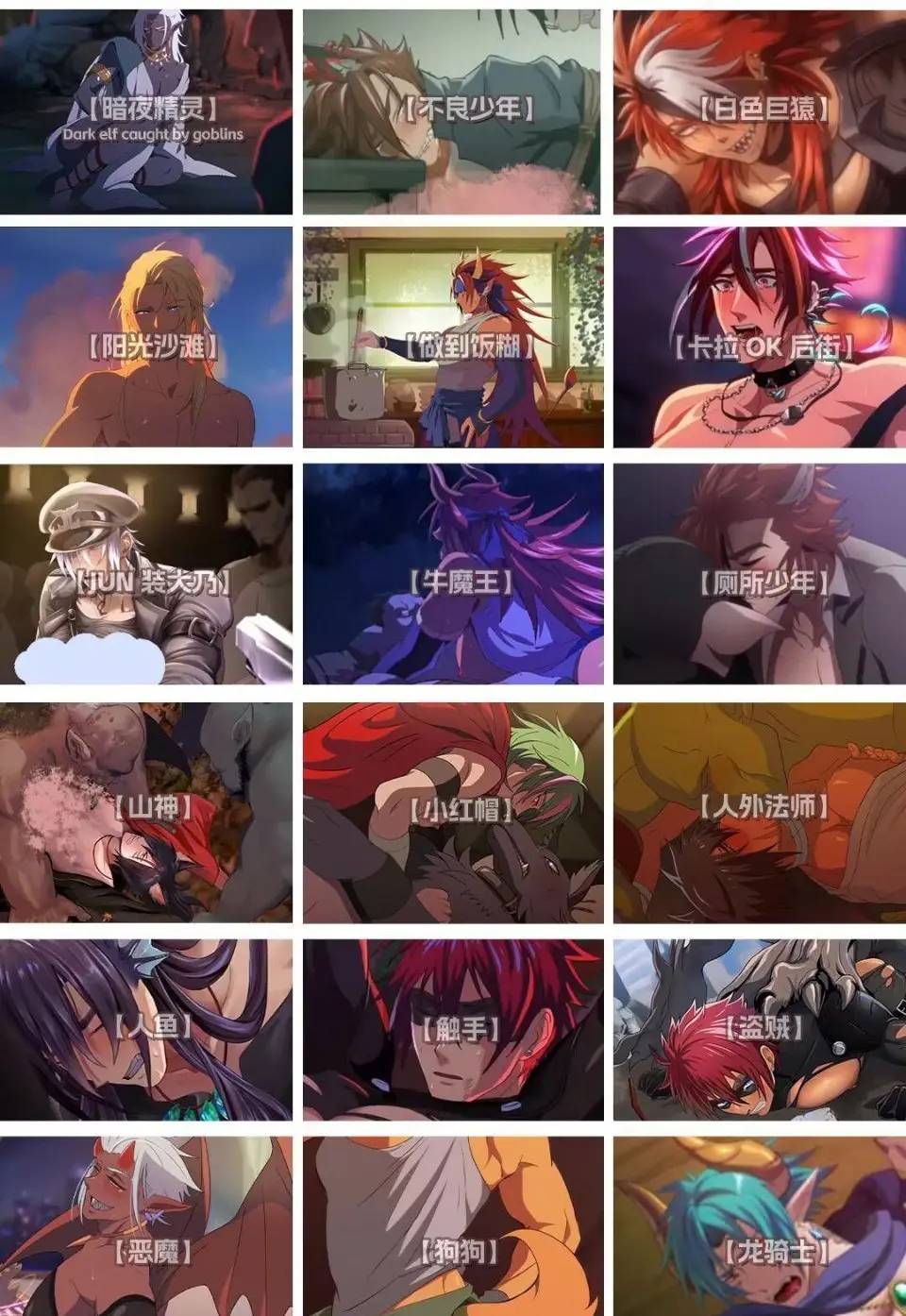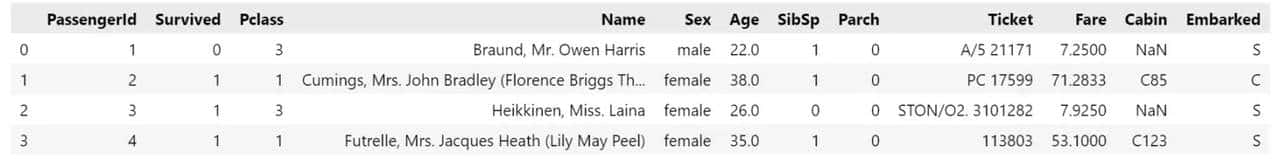大爷蹭八年银行空调,保安不驱赶,退休当天他说:快跟我来
六月的天,毒得像个后妈。
柏油马路被晒得滋滋冒油,空气里全是汽车尾气和灰尘混合的焦糊味。
我叫李伟,五十二,城东建设银行的保安,还差一个月退休。
我站在银行门口的阴凉里,后背的制服已经被汗溻透了,黏糊糊地粘在身上,像一块撕不掉的狗皮膏药。
银行的自动玻璃门“哗”地一声滑开,一股冷气夹杂着消毒水和钞票的混合味道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吸了一口。
一个瘦小的身影,趿拉着一双快磨平了的塑料拖鞋,贴着门边,像只壁虎一样溜了进来。
是陈大爷。
又是他。
八年了,只要银行开门,他准到。
他也不干啥,就在大厅角落那个没人坐的硬塑椅子上一待,从开门到关门。
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一把蒲扇,一个装着凉白开的大号搪瓷缸子,这就是他的全部装备。
行里的小年轻背后都叫他“空调显眼包”。
新来的大堂经理赵霖,上个月刚从总行空降下来,年轻气盛,看谁都不顺眼。
他用那支昂贵的钢笔敲着我的岗台,下巴抬得像只骄傲的公鸡。
“李师傅,咱们这是金融机构,不是慈善收容所。”
“那个天天来蹭空调的老头,影响我们银行的形象,你处理一下。”
我眼皮都没抬,“赵经理,人家没吵没闹,没影响任何客户,我按哪条规定处理他?”
赵霖被我噎了一下,脸有点挂不住,“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看看他那样子,客户进来怎么想?”
“客户想什么我管不着,我只管有没有人抢劫,有没有人闹事。”
我把胸口的保安证扶了扶,“这是我的职责。”
赵霖气得镜片后面的眼睛都瞪圆了,最后甩下一句“你!老油条!”,端着他的保温杯走了。
我心里冷笑,老油条?你小子吃的盐还没我吃的米多。
陈大爷像是没听见我们的争吵,依旧安静地坐在角落,慢慢地摇着蒲扇,眼神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好像灵魂出了窍。
今天又是这样。
他找了个最不碍事的角落,坐下,开始规律地摇扇子,仿佛那蒲扇能摇走的不只是暑气,还有时间。
我看着他,心里有点烦,又有点说不出的滋ou味。
我这辈子,最讲究的就是“规矩”二字。
当了二十年兵,规矩是刻在骨子里的。退伍后当保安,规矩是饭碗。
按规矩,陈大爷这种“闲杂人等”,我早就该把他“请”出去。
可八年了,我一次都没开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由于他那双眼睛,浑浊,却干净得像个孩子。
或许是由于他从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连上厕所都掐着人最少的时候去,出来还顺手把洗手台上的水渍擦干净。
也或许,是由于他跟我爸有点像,一样的沉默,一样的倔。
我爸走得早,要是活到目前,也该是陈大爷这个年纪了。
“哗——”
玻璃门再次打开,一个穿金戴银的胖女人扭了进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瞬间盖过了银行的消毒水味儿。
她一眼就瞥见了角落里的陈大爷,眉头立刻拧成了个疙瘩。
“哎哟,这什么味儿啊!”她夸张地捏住鼻子,对着柜员嚷嚷,“你们银行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啊?这老头坐这儿,我们还怎么办理业务?影响心情!”
她的声音尖利,整个大厅的人都看了过来。
陈大爷的身子僵了一下,摇扇子的手停住了,头埋得更低。
我胸口一股火“噌”地就上来了。
我走过去,挡在她和陈大爷中间,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这位女士,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她被我堵得一愣,“我取钱!你让开,先把他给我赶出去!看着就晦气!”
我脸上的笑容没变,声音却冷了下来。
“对不起,女士。我们银行开门迎客,来的都是客。这位大爷和您一样,也是我们的客户。”
“他?客户?”胖女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办什么业务?办‘蹭空调’业务吗?”
大厅里传来几声压抑的窃笑。
陈大爷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我直视着胖女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他办理的是‘安静地坐着,不打扰任何人’的业务。这项业务,您好像不太擅长。”
胖女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你一个臭保安!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要投诉你!”
“我的工号是0734,李伟。”我指了指胸牌,“投诉请便。目前,请您不要在大堂喧哗,影响其他客户。”
她大致没见过我这么硬气的保安,愣在那儿,气得嘴唇直哆嗦,半天说不出话。
最后,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剜了陈大oy一眼,“哼,跟穷鬼待一个屋,晦气!”说完,扭着腰,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了,钱也没取。
一场风波平息。
我回头看了看陈大爷。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但他对我,缓缓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点酸。
规矩是死的,但人心里的那杆秤,是活的。
日子一天天过。
赵经理找我谈了几次话,明里暗里地施压,我都用“军人作风”给他顶了回去。
他拿我没办法,毕竟我快退休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只能每天用眼刀子剜我和陈大爷,那眼神,好像我们俩是什么需要被清除的病毒。
我和陈大爷之间,依然没什么交流。
有时候我换班,会把没吃的包子塞给他。
他总是摆手,我就硬塞到他怀里,扭头就走。
第二天,我的岗台上会多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
我知道是他放的。
他大致是捡废品或者做点什么零工,买个苹果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顿午饭钱。
我老婆总说我死脑筋,不会“薅羊毛”,不会“打秋风”,活该一辈子当保安。
她说社区团购的团长,动动手指头一个月都能挣好几千,我守着个银行,连张免费的报纸都不知道往家拿。
我跟她吵:“那不一样!那是占公家便宜!”
她气得骂我:“你清高!你伟大!你拿清高伟大去给儿子交学费啊!”
儿子在读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
每次他打电话回来,第一句总是“爸,我妈呢?”,第二句才是“爸,我最近……”
我知道,他是想说生活费不够了,又不好意思直接跟我开口。
我心里发堵。
一个大男人,快退休了,连儿子的生活费都给得紧巴巴,的确 挺失败的。
那天,我看着陈大爷小心翼翼地啃着那个我给他的包子,突然在想,他有孩子吗?
他的孩子,会管他吗?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雨。
雨点子跟冰雹似的,砸在玻璃门上“噼里啪啦”响。
那天陈大爷来得特别晚。
他浑身湿透了,像只落汤鸡,裤腿上全是泥点子。
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找地方坐下,而是站在门口的地垫上,局促不安地往下滴着水,生怕弄脏了光亮的地板。
保洁阿姨看不过去,想拿拖把过来,被我拦住了。
我从我的储物柜里翻出一块旧毛巾,递给他。
“擦擦吧,陈大爷。”
他愣愣地接过,眼睛里有点红。
那天,他破天荒地跟我说了一句话,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
他说:“谢谢。”
我摆摆手,说:“没事儿。”
他擦干了头发和脸,走到柜台前,从怀里掏出一个被塑料袋裹了三层的布包。
他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深红色的存折。
他把存折递给柜员小王。
小王接过去,刷了一下,表情有点惊讶,抬头看了看陈大爷,又看了看我。
我心里好奇,但职责所在,不能离岗太近。
陈大爷没取钱,只是让小王查了查余额,然后又把存折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回怀里。
他走的时候,雨还没停。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第二天,小王趁着赵经理不在,偷偷跟我说。
“李哥,你知道吗?陈大爷那存折里,有三十万!”
我“啊”了一声,差点把手里的保温杯掉了。
三十万?
我以为我听错了。
一个天天来蹭空调,穿得破破烂烂,靠捡苹果换包子的老头,有三十万存款?
“而且,”小王压低声音,“那是笔定期,存了快八年了,一分没动过。”
八年。
他来银行,也是八年。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全乱了。
这算什么?真人版的“扫地僧”?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看懂过陈大爷。
他不是来蹭空调的。
他有钱,却过得像个乞丐。
他到底图什么?
这个疑问像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
我发现他每天都盯着大厅墙上的电子钟,眼神专注。
他不是在看时间,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时刻。
有一次,银行系统升级,电子钟黑屏了半天。
那半天里,陈大爷显得异常烦躁,不停地站起来,又坐下,蒲扇摇得飞快,毫无章法。
直到电子钟亮起,他才长长地舒了口气,重新恢复了那副雕塑般的样子。
他守着的,难道说是时间?
秋天的时候,陈大爷突然有三天没来。
第一天,我以为他有事。
第二天,我有点心慌。
第三天,我彻底坐不住了。
八年来,风雨无阻,他从没缺席过这么久。
我跟同事换了班,第一次在工作时间脱下了那身制服。
我凭着之前偶然瞥见他捡废品的路线,一路找到了附近的老城区。
那是一片快要拆迁的棚户区,巷子窄得只能过一辆自行车,空气里弥漫着潮湿和腐朽的气味。
我挨家挨户地打听,形容着陈大爷的模样。
一个在门口择菜的大妈指了指巷子最深处一个低矮的小平房。
“你说的是陈木匠吧?就住那儿,不过他好像病了,两天没出门了。”
我心一沉,快步走过去。
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药味和霉味扑鼻而来。
屋里很暗,唯一的窗户被报纸糊着。
陈大爷躺在一张硬板床上,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薄被,脸色蜡黄,呼吸微弱。
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已经冷掉的白粥和几片廉价的感冒药。
我叫了他几声,他才缓缓睁开眼。
看到是我,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赶紧按住他,“别动,您病了。”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不行,得去医院!”
我二话不说,背起他瘦小的身躯就往外走。
他比我想象的要轻得多,像一捆干枯的柴火。
他趴在我背上,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不去……不去医院……费钱……”
“钱什么钱!命重大!”我吼了他一句。
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大声说话。
他没再做声,只是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脖子上。
到了医院,挂号、缴费、做检查,我跑前跑后。
医生说是急性肺炎,加上营养不良,得住院。
我没犹豫,用我自己的工资卡交了住院费。
办完手续,我坐在病床边,看着他打着点滴,终于安稳地睡着了。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给他蜡黄的脸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存折里有三十万的人,病了却舍不得去医院,宁愿自己硬扛。
这已经不是“节俭”能解释的了。
这是一种近乎自虐的执拗。
那一刻我才清楚,可怜之人,往往有更可怜之处。
陈大爷住院一个星期,都是我跟老婆轮流去照顾。
老婆嘴上抱怨我多管闲事,但每次煲的鸡汤都装得满满当当。
出院那天,我去接他。
他换上了我给他买的新衣服,人看着精神了不少。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存折,非要塞给我。
“小李,住院的钱,还有……这些,你拿着。”
我把存折推回去,脸一板,“陈大爺,你这是打我的脸!我当你是长辈,你当我是什么?图你钱?”
他眼圈红了,拿着存折的手微微颤抖。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打断他,“钱你收好,后来按时吃饭,别再生病了。”
我把他送回那个小平房。
临走时,我还是没忍住,问出了那个憋了很久的问题。
“陈大爷,我能问问吗?您守着那笔钱,又不用,到底是为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转过身,看着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唯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笑得像花儿一样的年轻姑娘,梳着马尾辫,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那是我闺女。”他声音嘶哑,“八年前,她就在你们银行门口,出车祸走的。”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有惊雷炸开。
我呆立当场,如遭雷击。
“她……她叫陈晓燕,以前也是你们银行的柜员。”
陈晓燕!
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
八年前,我刚来这个网点不久。的确 有个年轻姑娘出了事,当时行里还组织了捐款。
但我从没把她和眼前这个孤苦的老人联系在一起。
“那笔钱,是肇事司机的赔偿款。”
“我一个子儿都没动。”
“我总觉得,动了那钱,我闺女就真的没了。”
“我每天去银行,不是蹭空调。我就是想……离她近一点。”
“她最喜爱那份工作了,每天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跟我说‘爸,我去上班啦’。”
“我就坐在那儿,看着那个钟,就好像她还没下班,我还在等她回家。”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八年。
整整八年。
他不是在守着一笔钱,他是在守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最后的念想。
他不是在等时间,他是在对抗时间,妄图让时间停留在女儿还活着的昨天。
而我,这个自诩看透人情世故的老兵,这个讲规矩讲原则的保安,八年来,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我甚至还由于他“蹭空调”而烦恼过,由于他“有钱不用”而困惑过。
我真是个眼瞎心盲的混蛋!
我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陈大爷吓了一跳,“小李,你这是干什么!”
我抓住他的手,哽咽着说:“大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他反过来拍着我的背,像安慰一个孩子。
“不怪你,不怪你……你是个好人。”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陈大爷还是每天来银行,但我看他的眼神,已经完全不同。
我不再当他是需要照顾的孤寡老人,我当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一个战友。
他守着他的女儿,我守着他。
赵经理依然看我们不顺眼。
有一次,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陈大爷说:“李伟,今天你要是不把他请出去,我就给总行保安部打电话,说你渎职!”
这是最后通牒了。
同事们都替我捏了把汗。
我走到赵经理面前,站得笔直,像一棵松树。
“赵经理,在我退休之前,这里,我说了算。”
“这位陈大爷,他不是闲杂人等。他是我们银行一位已故优秀员工的父亲。”
“他每天来这里,是看望他的女儿。”
“我们银行的企业文化,我记得有一条是‘人文关怀’。如果连这样一位父亲都容不下,那这四个字,就是个笑话。”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铿锵有力。
整个大厅鸦雀无声。
赵经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像开了染坊。
他大致没想到我会把事情捅出来,更没想到会扯上“企业文化”的高度。
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灰溜溜地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从那后来,再也没人敢对陈大爷指指点点。
行里的小年轻们,看他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尊敬。
有人会悄悄给他递上一杯热水,有人会把自己的午餐分他一半。
陈大爷还是那个沉默的陈大爷,但他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很快,就到了我退休的日子。
最后一天上班,我特意早早地到了。
我把那身穿了十几年的制服熨烫得笔挺,把帽檐上的警徽擦得锃亮。
我像个新兵一样,在银行门口站岗,迎来送往。
每一个进出的熟客,都笑着跟我说:“李哥,祝贺退休啊!”
“李师傅,后来常回来看看!”
我笑着一一回应,心里却空落落的。
就像一棵树,长在一个地方太久了,突然要被连根拔起,总会带着许多泥土和不舍。
陈大爷和平时一样的时间到了。
他今天没拿蒲扇,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
他走到我面前,把布袋子递给我。
“小李,祝贺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双崭新的手工布鞋,鞋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针脚细密。
“我以前是木匠,手上还有点活儿。给你做的,别嫌弃。”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大爷,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他笑了,脸上常年紧绷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风干的菊花,“你穿着合脚就行。”
下午五点,银行准时关门。
我和同事们一一拥抱告别。
我脱下制服,换上便装,把储物柜清空,钥匙交还给办公室。
当我走出银行大厅时,我感觉自己像个卸了甲的士兵,一身轻松,又无限怅惘。
我看到陈大爷还坐在那个角落里,没有走。
他在等我。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爷,我走了。后来……您自己多保重。”
他站起身,定定地看着我。
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小李,快跟我来。”
我愣住了。
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浑浊和悲伤,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亮和急切。
“大爷,去哪儿?”
“别问,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他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就往外走。
他的手很干瘦,但很有力。
我满腹疑窦,但还是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我们没有走向他住的那个棚户区。
他带着我,穿过马路,走进了银行对面的一个高档小区。
这个小区我熟悉,房价贵得吓人,住的非富即贵。
他怎么会来这里?
他熟门熟路地走进一栋楼,没有按门禁,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门禁卡,“滴”的一声刷开了单元门。
我更懵了。
我们走进电梯,他按了16楼。
电梯里光洁如镜,映出我俩的身影。
一个穿着崭新布鞋的退休保安,一个穿着洗白褂子的神秘老头。
这组合,怎么看怎么诡异。
电梯门打开,是一条安静的走廊。
他领着我,走到1602的房门前,从口袋里又摸出一串钥匙,熟练地打开了房门。
“进来吧。”
我迟疑地踏进房间。
然后,我彻底惊呆了。
这不是一个家。
这是一个……纪念馆。
房子很大,至少一百五十平,装修得简洁雅致。
但屋里几乎没有什么生活气息。
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同一个女孩的照片。
从她咿呀学语,到她上学,到她毕业,到她穿着银行制服对着镜头甜甜地笑。
是陈晓燕。
客厅中央的茶几上,没有茶具,只有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相框。
相框里,是陈晓燕的黑白照。
照片前,放着一个新鲜的苹果。
整个房间一尘不染,干净得不像有人住。
“这……这是……”我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这是我给晓燕买的婚房。”
陈大爷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是压抑了八年的深海。
“她出事那年,本来准备要结婚了。”
“房子刚装修好,她一天都还没住过。”
“她走后,那个男方……就没再联系过。”
“我就把这里,照着她喜爱的样子布置好。”
“我不住这儿,我怕……我怕把这里弄脏了。”
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对面建设银行的大门。
看到我站岗的那个位置。
“我每天,就在对面的小屋里住着。然后来银行坐一天,晚上再回到这里,给她擦擦照片,跟她说说话。”
“我就想,她每天上班下班,都能看到我。”
“我就想,我每天,也能看到她工作的地方。”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终于全清楚了。
他守着三十万不敢动,是守着女儿的“命”。
他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不住,是守着女儿未完成的“家”。
他守在银行的大厅里,是守着女儿最后的“身影”。
他守着一个念想,而我,守了他八年。
我这个傻子,还真以为他是为了那点空调费。
我真是又蠢又可笑。
“大爷……”我的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了。
他转过身,从卧室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
“小李,这是这房子的房产证,还有那个存折。”
我吓得连连后退,“大爷,您这是干什么!使不得!这绝对使不得!”
“你听我说完。”他按住我的肩膀,眼神无比郑重。
“我没有别的亲人了。这房子,这钱,留着对我来说,就是个念想,也是个负担。”
“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哪天就走了。这些东西,不能就这么没了。”
“你是个好人。这八年,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儿子要上大学,要花钱。这房子,你卖了也好,租了也好,就当是我……是我替晓燕,谢谢你。”
“谢谢你这八年,没有赶我走。”
“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背我去医院。”
“谢谢你,像个儿子一样,给我买衣服,给我送饭。”
“你守了我八年,目前,该轮到我,或者说,轮到晓燕,来守着你了。”
我拼命摇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行!我不能要!这是您女儿留给您的!我怎么能要!”
“你不要,我又能给谁呢?”他惨然一笑,“难道说要我带到骨灰盒里去吗?”
“小李,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我不想让晓燕留下的东西,最后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
他把文件袋硬塞到我怀里,那重量,仿佛有千斤重。
我拿着那个文件袋,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要?还是不要?
理智告知我,这绝对不能要。这是不义之ABC。
但情感上,我看着眼前这个孤苦的老人,看着他那双充满恳求和托付的眼睛,我怎么忍心拒绝?
拒绝,对他来说,也许是更残忍的。
那意味着,他女儿留下的最后一点价值,也被否定了。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浆糊。
钱,房子,尊严,情义……所有东西都搅在一起。
我突然想起了我老婆。
她总骂我死脑筋,不会变通。
如果她知道这件事,她会怎么说?她会让我收下吗?
我甚至想到了那个喜爱在短视频平台刷“人生逆袭”的儿子。
如果他知道他爸突然有了一大笔钱,他会是什么反应?是高兴,还是会问钱的来路?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我抬起头,看着陈大爷。
“大爷,这房子,这钱,我不能白要。”
“但我可以替您保管。”
陈大爷愣住了,“保管?”
“对。”我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也许是我这辈子最重大的决定。
“我们成立一个基金会,就用晓燕的名字命名,叫‘陈晓燕助学基金’。”
“这笔钱,这套房子卖掉的钱,全部放进去。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像晓燕一样优秀,但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您来当会长,我给您跑腿,当秘书长。”
“这样,晓燕的爱心,可以协助更多的人。她的名字,也会被更多的人记住。”
“这笔钱,不再是死的赔偿款,它活了。您的女儿,也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了无数人的生命里。”
陈大爷呆呆地听着,浑浊的眼睛里,一点点地亮起了光。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像是熄灭了八年的灰烬,重新燃起了火星。
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一个字地问:“真……真的可以吗?”
“可以!必定可以!”我用力地点头,“我们明天就去咨询律师,办手续!”
他突然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我。
一个瘦小干枯的身躯,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我听见他压抑了多年的哭声,在我耳边嚎啕而出。
那哭声里,有悲伤,有思念,有委屈,但更多的,是释放,是解脱。
我也抱着他,任由眼泪打湿他的肩膀。
那一刻,我们不是保安和老人,不是施舍者和被同情者。
我们是两个男人,两个父亲,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找到了彼此的温暖。
人心不是铁打的,焐一焐,总会热的。
一年后。
“陈晓燕助学基金”正式成立。
第一批资助了五个大学生。
捐赠仪式上,陈大爷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胸前戴着红花,作为基金会会长发言。
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畏畏缩缩的老头。
他站在台上,背脊挺直,声音洪亮。
他说:“我女儿没走远,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大家一起上大学。”
台下掌声雷动。
我站在台下,看着他,眼眶湿润。
仪式结束后,赵经理特意跑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
“李哥,我错了。我为我以前的无知和傲慢,向您和陈大爷道歉。”
我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年轻人,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
如今,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陪着陈大爷处理基金会的事务,去各个大学考察申请的学生。
我们一起坐公交,一起吃路边摊的牛肉面,一起为了一个学生的资格争得面红耳赤。
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身体也越来越硬朗。
他不再去银行了。
他说,晓燕已经不在那个小小的房子里了,她去了更远,更广阔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路过那家银行,我还会习惯性地朝里面望一眼。
新的保安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得笔挺。
大厅里人来人往,一切如常。
仿佛那八年的时光,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场梦。
但那双手工纳的布鞋,我还穿着。
它提醒我,我曾用八年的“不合规矩”,守住了一个父亲最后的尊严。
也守住了,一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善良。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操蛋,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