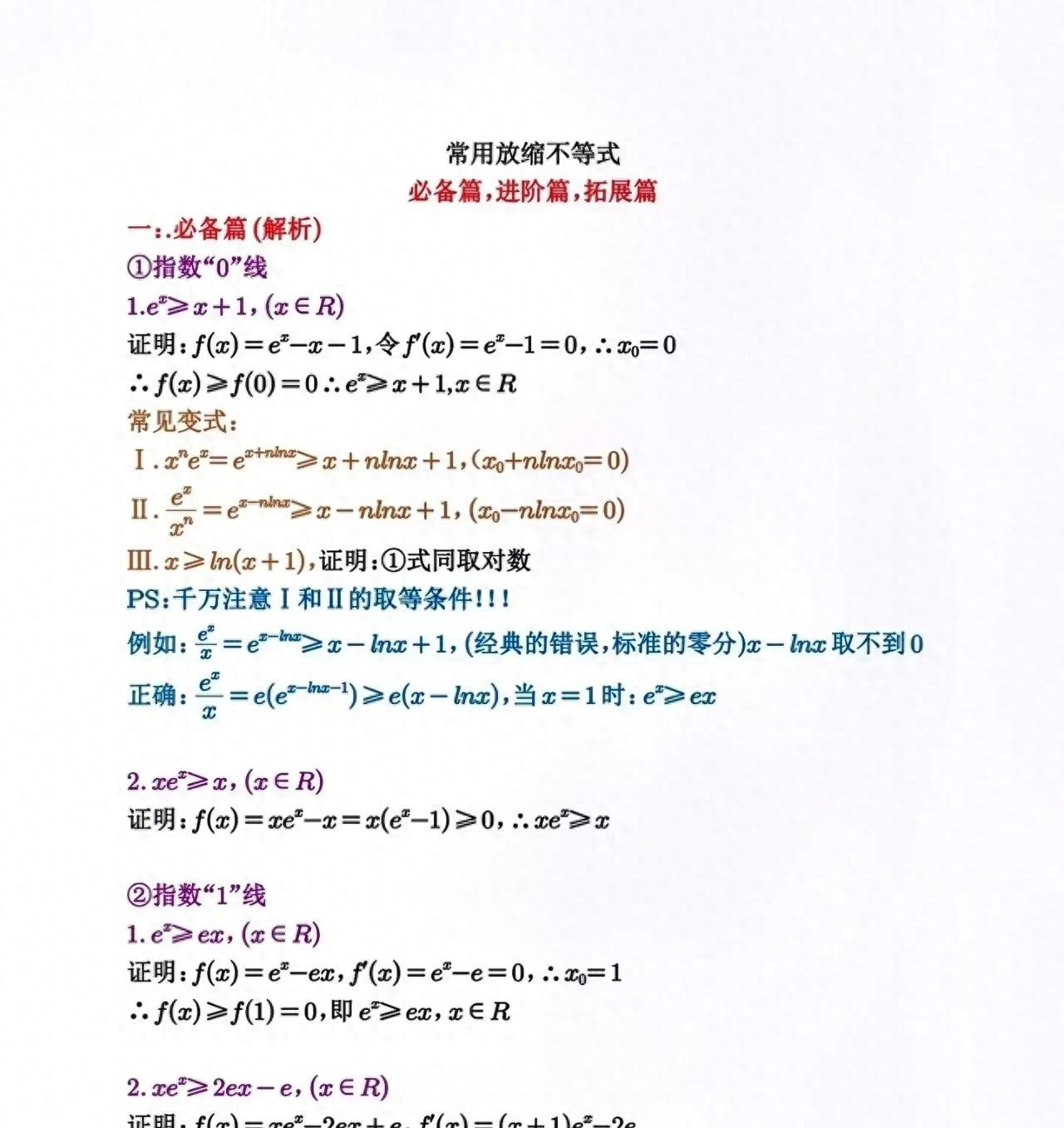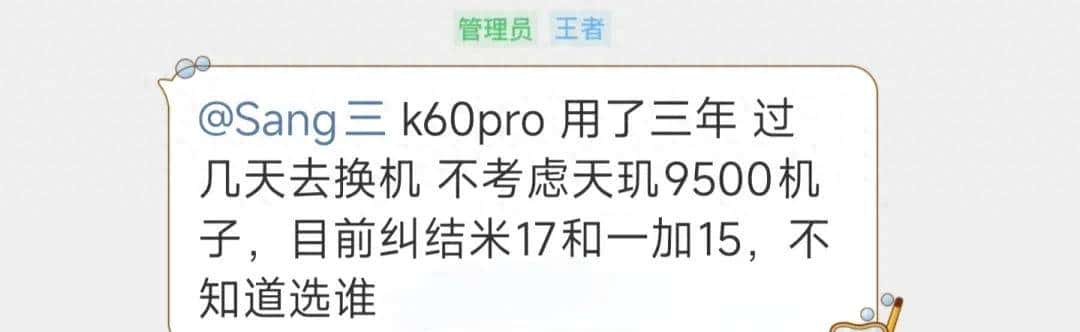第二天,林薇的工位空了。
桌上的那盆小多肉,叶片已经微微发蔫,旁边还放着她没来得及喝完的半杯咖啡,一切都像是主人只是暂时离开,很快就会回来。但我们都知道,她不会回来了。
从我们搭档“绿洲计划”开始,整整三个月,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我曾以为我们是战友,是那种在项目攻坚战里,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伙伴。直到晋升名单公布,她的名字赫然在上,而我,成了她成功故事里一个无声的注脚,甚至连注脚都算不上。
那一晚,她在部门群里意气风发地宣布请客,庆祝她的“实至名归”。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我看着群里不断刷新的“祝贺”和“薇姐威武”,感觉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一点点收紧,几乎喘不过气。
而这一切,都要从三个月前,张总把那个被称为“烫手山芋”的“绿洲计划”交给我们说起。
第1章 烫手的山芋
“绿洲计划”,名字听着充满生机,实际上却是公司去年遗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这是一个旨在优化客户数据管理系统的项目,前一个团队做了半年,不仅没拿出成果,反而把系统底层搞得一团糟,最后负责人引咎辞职,项目也就此搁置。
张总把我和林薇叫进办公室的时候,表情严肃得像是在宣布一场战争的开始。
“陈阳,林薇,”他指了指桌上厚厚一叠的文件,“‘绿洲计划’,公司决定重启。我知道这块骨头难啃,但啃下来,对你们俩的履历,对公司,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是技术部的老黄牛,擅长埋头解决技术难题,但对这种涉及多部门协调、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的项目,本能地有些畏惧。
林薇却显得很兴奋,她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光:“张总放心,我们必定全力以赴。”
我看了她一眼。林薇比我晚两年进公司,但人很活络,能说会道,尤其擅长向上管理,跟各部门关系都处得不错。张总把我们俩搭在一起,用意很明显:我的技术,配她的协调能力,或许能把这个项目盘活。
走出办公室,林薇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轻松:“陈阳,别愁眉苦脸的。这可是个机会。有你的技术兜底,我负责冲锋陷阵,咱们俩,绝配。”
她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我想,或许她说得对,团队合作,各展所长,没什么可怕的。
那之后,我们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并肩作战。
说是并肩作战,实则更像是我在挖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而林薇负责在洞口给我递工具和水。项目的核心技术难题,几乎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前任团队留下的代码像一团缠绕的乱麻,我只能一根一根地拆解,重构。
那段时间,办公室的灯几乎每晚都是为我而亮。我的工位上,堆满了各种技术文档和草稿纸,外卖盒子摞得老高。林薇的确 也尽心尽力,她负责和产品、市场等各个部门沟通需求,整理反馈,把所有的外部信息处理得井井有条,让我能专心致志地对付那些恼人的代码。
她会记得给我带早餐,提醒我喝水,甚至在我熬得双眼通红的时候,泡一杯浓浓的咖啡放在我手边,温柔地说:“阳哥,辛苦了。进度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协调的吗?”
我记得有一次,为了解决一个关键的算法瓶颈,我连续在公司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凌晨四点,我终于在测试环境跑通了模型,疲惫地靠在椅子上,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
林薇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递给我一条温热的毛巾:“快擦擦脸,看你憔悴的。我给你点了粥,马上就到。”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觉得,能有这样一个体贴、能干的搭档,是我的幸运。我毫无保留地和她分享我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技术突破。我把整个项目的底层架构、核心代码逻辑,像讲故事一样,一点一点地剖析给她听。
“你看这里,”我指着屏幕上的一段复杂代码,“我用了一个递归算法,虽然绕了点,但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冗余,运行效率能提升至少百分之三十。”
她听得特别认真,不住地点头,还拿着本子做笔记。“阳哥,你太厉害了!这些我得好好消化一下,下次跟产品部那边沟通,我心里就有底了。”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团队内部正常的知识同步。我甚至觉得,我不仅是在完成一个项目,还在培养一个默契的战友。我天真地以为,功劳簿上,我们俩的名字会紧紧挨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项目中期,我们一起向张总做汇报。林薇主讲,我做技术补充。她口才极好,把我们遇到的困难、我的技术方案,以及项目的未来前景,描绘得生动而清晰。张总听得频频点头,看向我们的眼神里满是赞许。
汇报结束后,张总特意把我留下,拍着我的肩膀说:“陈阳,干得不错。你这块金子,这次总算要发光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我甚至开始畅想,项目成功后,我或许能评上高级工程师,工资也能涨一大截,到时候就能把老家的父母接过来住一段时间了。
我沉浸在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战友”,看我的眼神,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第2章 微妙的裂痕
裂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许它一直都在,只是我被“战友情”的幻象蒙蔽了双眼,选择性地忽略了那些不和谐的音符。
第一次感到不对劲,是在一次跨部门的周会上。
那次会议主要是向市场部和运营部的同事同步“绿洲计划”的最新进展。按照我们之前的分工,我负责讲解技术实现的部分,林薇负责讲解产品逻辑和应用前景。
会议开始前,我还在调试投影仪,林薇拿着她的笔记本电脑走过来说:“阳哥,今天技术那块我来讲吧。你熬了好几个通宵,肯定也累了,正好休憩一下。放心,你之前讲给我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
我愣了一下,有些意外。但看她一脸真诚的笑容,又觉得是自己多心了。或许她只是想多锻炼一下,也想在其他部门同事面前展示我们团队的全面性。
“行,那你讲。有什么细节问题,我再补充。”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会议开始了。林薇站在台前,侃侃而谈。她的确 很机智,把我讲给她听的那些技术要点,用一种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转述了出来,甚至还加入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市场部和运营部的同事听得连连点头,显然对这种“去技术化”的讲解超级受用。
不过,讲着讲着,我就感觉味道不对了。
她开始频繁地使用“我”作为主语。
“在设计底层架构时,我思考了三种方案,最终选择了目前这个,由于它在扩展性上更有优势。”
“这个数据加密算法,是我反复调试了近一个星期才找到的最优解。”
“为了解决前端的兼容性问题,我重写了大部分的渲染逻辑。”
我坐在台下,手心开始冒汗。她说的每一个“我”,背后都是我通宵达旦的身影。那些技术难点,那些复杂的代码,是我一行一行敲出来的,是我在无数次失败和重试中摸索出的道路。而目前,这些成果从她嘴里说出来,仿佛都成了她一个人的功劳。
她讲得太流畅,太自然了,就好像她真的亲身经历过那些绞尽脑汁的夜晚。
会议中途,市场部的总监提了一个关于数据并发处理的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很刁钻,直指系统的核心瓶颈。我正准备开口补充,林薇却微笑着摆了摆手,示意她来回答。
她用我之前跟她分析的思路,条理清晰地阐述了一遍,虽然在一些关键参数上说得有些含糊,但足以应付非技术人员的提问。
那一刻,我看着聚光灯下的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种陌生的、冰冷的疏离感,第一次在我们之间升起。
会议结束后,几个同事围住林薇,纷纷称赞:“薇薇,真没看出来,你不仅沟通能力强,技术也这么牛!”
“是啊,后来我们部门有什么技术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找你了?”
林薇笑着,一一回应,游刃有余。她没有看我,一眼都没有。
我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电脑,一个人走回工位。那种感觉很复杂,有愤怒,有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困惑。我不清楚,我们不是战友吗?为什么要这样?
那天下午,林薇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身边,语气和往常一样亲切:“阳哥,今天会上讲的还行吧?没给你丢人吧?”
我看着她,想问她为什么要那么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该怎么问?问她为什么要把我的功劳说成是她的?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太小气,太计较?我们还要继续合作,把关系闹僵了,项目怎么办?
我最终只是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讲得挺好的。”
她似乎松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胳膊:“那就好。主要是我觉得,技术的东西,由我这个项目经理的口说出来,可能高层听起来会更‘整体’一些。你懂的,这是汇报技巧。”
汇报技巧?我心里冷笑。原来把别人的心血说成是自己的,也算是一种技巧。
从那天起,我心里埋下了一根刺。我开始留心她的一举一动。我发现,她向张总汇报工作时,越来越少地提及我的名字。她发出的项目周报里,工作成果的陈述,主语也悄悄地从“我们”变成了“我”。
我开始留了个心眼。每次完成一个重大的模块,我都会在代码的注释里,加上一个只有我自己能看懂的标记——我的名字缩写和当天的日期。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保护,像小动物在自己的领地里留下气味。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但至少能给我一点心理安慰。
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作量越来越大,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纯粹而公式化。她给我提需求,我完成,然后交付。那些深夜的咖啡和热粥,再也没有出现过。办公室里只剩下键盘的敲击声,和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的沉默。
我依然在拼命,由于我想完成这个项目,我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告知自己,只要项目成功了,公司高层自然会看到谁才是真正的核心。
目前想来,那时候的我,真是天真得可笑。
第3章 尘埃落定
项目终于在预定的死线前三天,完成了最终的测试和部署。
当我在服务器上敲下最后一行指令,看到系统平稳运行的绿色提示时,积压了三个月的疲惫和压力,瞬间像潮水般退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林薇站在我身后,也显得很激动。她用力地抱了我一下,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阳哥,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那一刻,所有的不快和猜忌似乎都暂时被抛到了脑后。成功的喜悦是真实的,我们共同为此付出了太多。我拍了拍她的背,由衷地说:“是啊,成功了。大家都不容易。”
第二天,我们向公司最高管理层做了最终的项目成果汇报。
这次汇报,林薇准备得极其充分。PPT做得精美绝伦,每一页的数据和图表都极具说服力。她站在台上,神采飞扬,从项目背景,到技术创新,再到商业价值,讲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
她再次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里,我的名字只在开头介绍团队成员时被一笔带过。她巧妙地将我描述成一个“提供技术支持”的辅助角色,而她自己,则是那个运筹帷幄、攻克所有难关的灵魂人物。
我坐在台下,听着她把我熬了无数个夜晚才攻克的技术难点,轻描淡写地描述为“我当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心里已经麻木了。
我看着台上的CEO、CTO频频点头,看着张总脸上欣慰的笑容,我知道,大局已定。
这场精心编排的独角戏,演得天衣无缝。而我,连一个提词的配角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坐在观众席里的“知情者”。
汇报结束,掌声雷动。CEO当场宣布,“绿洲计划”是公司今年最成功的技术革新项目,要对项目组进行通报表彰和奖励。
林薇在掌声中向大家鞠躬,眼眶微微泛红,像是激动,又像是感慨。她走下台,经过我身边时,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你,陈阳。”
那句“谢谢”轻飘飘的,像一根羽毛,却刺得我心口生疼。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会议室的。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却感觉浑身发冷。
接下来的几天,公司里到处都在讨论“绿洲计划”的成功和林薇的出色表现。她的名字成了“年轻有为”、“能力出众”的代名词。而我,依然是那个坐在角落里默默无闻的程序员陈阳。
一周后,公司内部发布了新的人事任命。
林薇,晋升为技术部高级经理,成为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门经理之一。
公告邮件弹出来的那一刻,整个办公室都沸腾了。同事们纷纷涌向林薇的工位,向她道贺。
“薇姐,祝贺祝贺!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后来要多关照我们啊,林经理!”
“今晚必须请客啊!”
林薇被簇拥在人群中间,笑得灿烂又得体。她目光扫过办公室,最后落在我身上,与我对视了短短一秒。那眼神很复杂,有得意,有炫耀,或许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愧疚。
我面无表情地把目光移回自己的电脑屏幕,屏幕上还显示着“绿洲计划”的源代码。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符,像一个个嘲讽的笑脸,在我眼前跳动。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一点点变凉,最后凝固成冰。
三个月的拼命,三个月的付出,最后只换来一句轻飘飘的“谢谢”,和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我像一个辛辛苦苦种了一季稻谷的农民,眼睁睁看着别人在丰收的庆典上,将我所有的收成都据为己有,还宣称是她自己亲手播种、浇灌的。
荒谬,又可悲。
那天下午,部门群里,林薇发了一个红包,然后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感谢公司对我的认可,感谢张总的栽培,也感谢项目组所有小伙伴的支持。今晚七点,我在‘海天阁’订了包厢,庆祝这次晋升,也为了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协助,希望大家都能赏光参与!”
消息一出,群里立刻被各种“必定到”、“薇姐大气”的表情包刷屏。
我看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
去,还是不去?
去了,是亲眼见证她的春风得意,是用自己的沉默来为她的谎言背书。
不去,又显得我小气、输不起。
最终,我回了一个字:“好。”
我想去看看。我想亲眼看看,一个人的意气风发,可以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累累白骨之上到何种地步。
我也想给自己一个最后的了断。这场压抑了许久的独角戏,是时候该落幕了。
第4章 庆功晚宴
海天阁是城里有名的海鲜酒楼,装修得富丽堂皇,一个包厢的最低消费就抵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林薇这次,的确 是下了血本。
我到的时候,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热闹非凡。林薇穿着一条精致的连衣裙,化着淡妆,正在席间穿梭,招呼着每一位同事,俨然是全场的焦点。
她看到我,眼睛一亮,主动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腕:“阳哥,你来啦!快坐,今天你可是大功臣,必须坐主位!”
她笑得那么亲切自然,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芥蒂,依然是那对亲密无间的“战友”。
周围的同事立刻起哄:
“对啊,陈阳这次也是辛苦了,必须多喝几杯!”
“薇姐,你可得好好敬陈阳一杯,听说项目最难的技术都是他搞定的。”
说这话的同事,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想看热闹。
林薇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但立刻又恢复如常。她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着众人朗声说道:“那当然!我和陈阳是什么关系?过命的交情!这个项目,没有他,绝对不可能成功。来,陈阳,我敬你第一杯!我干了,你随意!”
她端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动作豪爽,引来一片叫好声。
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丝毫波澜。我端起酒杯,也喝了一口,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像火在烧。
整场晚宴,林薇都在极力地“表扬”我。她把我的角色定位成一个任劳任怨、技术过硬、但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而她,则是那个慧眼识珠、知人善用、将英雄推向前的“伯乐”和“领导者”。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不动声色地抬高自己,同时又显得那么“顾及情分”。
“我们陈阳,就是性格太内向了,不爱说话。但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当时那个核心算法,他一个人关在小黑屋里琢磨了三天三夜,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充满了赞许和“爱护”。
“后来我当了经理,第一个就要重用陈阳这样的人才。踏实,肯干,是咱们部门的定海神针。”她举着酒杯,向我示意,像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
同事们听着,都纷纷点头,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们大致觉得,林薇真是一个懂得感恩、不忘旧情的好领导。
而我,坐在那里,像一个被精心打扮的木偶,配合着她上演一出“将相和”的戏码。我没有反驳,没有辩解,只是安静地吃菜,喝酒。
我的沉默,在别人看来,或许是默认,是老实人的不善言辞。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等。等一个时机,等一个最适合开口的瞬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厢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大家开始玩起了游戏,输的人罚酒。林薇显然是今晚的主角,也是被灌酒的主要对象。她酒量似乎不错,来者不拒,脸颊泛着兴奋的红晕。
在又一轮的游戏里,林薇输了。她笑着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这杯酒,我要单独敬张总。没有张总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绿洲计划’的今天,更没有我的今天!”
张总笑呵呵地站起来,和她碰杯:“说到底,还是你们自己争气。尤其是你,林薇,这次表现的确 亮眼,有勇有谋,是个将才。”
林薇的眼睛更亮了,她一口喝干杯中酒,然后转向我说:“阳哥,下一杯,我们俩单独喝一个。千言万语都在酒里了。后来,我们还要继续当最好的搭档!”
她给我倒满了酒,也给自己倒满。
整个包厢的人都安静下来,看着我们。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酒杯,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志得意满的光芒。我知道,时机到了。
我慢慢地站起身,没有去接她手里的酒杯。
我拿起自己的手机,解锁,点开了部门的微信群。
我对她笑了笑,那大致是我这辈子笑得最冷的一次。
“酒先不喝。”我说,“在喝这杯酒之前,我想先在群里分享一个东西,也算为这次庆功宴助助兴。”
第5章 一句话的重量
我的话音不高,但在喧闹过后的包厢里,却显得异常清晰。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身上,带着不解和好奇。林薇举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
“陈阳,你……要分享什么?”她试探着问,语气里透着一丝警惕。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手指在上面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
整个包厢里,安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同事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总也皱起了眉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询问。
我能感觉到林薇的目光,像两道利剑,死死地钉在我身上。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此刻内心的惊涛骇浪。
终于,我编辑好了那句话,检查了一遍,然后按下了发送键。
“嗡——”
几乎是同时,包厢里所有人的手机都震动了一下。这是微信群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
大家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看向屏幕。
我也抬起头,迎向林薇的目光,然后,一字一顿地,把我刚刚发到群里的那句话,轻声念了出来:
“林经理,再次祝贺你高升。说起来,‘绿洲计划’最终版的交付代码包里,我当时为了方便调试,在核心框架的注释里留了一个个人标记,是一个Base64加密的字符串,写的是‘Created by Chen Yang, on 20231026’。这个标记应该不影响系统运行,你提交给公司存档的时候,应该……没删掉吧?”
话音落下,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看到林薇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毫无血色。她手里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一地晶莹的玻璃碴,酒液溅湿了她美丽的裙摆,她却毫无反应。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着,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恐惧,和难以置信。
包厢里的其他人,先是茫然,然后慢慢地,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们看看手机群里的那句话,又看看脸色煞白的林薇,再看看平静地站在那里的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尴尬和震惊。
没有人是傻子。
我这句话里,信息量太大了。
第一,我明确指出了代码核心框架里有我的个人标记。
第二,我点出了标记的具体内容和创建日期。
第三,我用了一个看似无意的问句,“你应该没删掉吧?”,这既是提醒,也是将军。
如果她说删掉了,那就等于承认她看过、并且刻意抹去了我的痕迹,是做贼心虚。
如果她说不知道,那她连自己项目核心代码里有什么都说不清楚,她这个“总负责人”的身份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而最致命的是,那个代码包,作为项目最终成果,肯定已经在公司服务器上存档备案了。这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验证的、铁一样的实际。
张总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猛地站起来,死死地盯着林薇,声音低沉得可怕:“林薇,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林薇浑身一颤,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她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她当然知道是真的。
由于我说的那个标记,我曾经当着她的面,作为一个小玩笑,指给她看过。
那是在项目攻坚最紧张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你看,我在这里留个记号,后来这套代码成了传奇,别人还能知道它的作者是谁。”
当时她还笑着说:“行啊,就当是你的签名了。”
她大致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个细节。或者,她根本就没把这个细节放在心上。她太自信,也太轻视我了。她以为我这个老实巴交的技术宅,就算受了委屈,也只会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绝对没有胆量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一种方式,把事情捅出来。
她错了。
兔子急了也咬人。何况,我不是兔子,我只是一个不想让自己的心血被人随意践踏的普通人。
“我……”林薇终于发出了一点声音,脸色比地上的碎玻璃还要惨白,“我……张总,我……”
她“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辩解。
由于实际,是无法辩解的。
张总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转向我,眼神复杂。有震惊,有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 Veľké的赞许。他大致也没想到,我这个平时闷声不响的老黄牛,会用如此精准而致命的一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好了,”张总深吸一口气,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今天的晚宴,就到这里吧。大家……都先回去。”
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同事们如蒙大赦,纷纷起身,低着头,谁也不敢多看一眼,匆匆离开了包厢。仿佛多待一秒,就会被这场风暴的余波卷进去。
很快,偌大的包厢里,只剩下我,张总,和瘫坐在椅子上,失魂落魄的林薇。
第6章 空荡的工位
张总没有再看林薇一眼,他只是走到我面前,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陈阳,跟我来一下。”
我点点头,跟着他走出了包厢。经过林薇身边时,我没有侧目。我不想看她目前的样子,那没有意义。这场闹剧,从我发出那条信息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酒店安静的走廊里,谁都没有说话。直到走到一个无人的露台,张总才停下脚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摇了摇头:“谢谢张总,我不会。”
他自己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夜色中很快散去。
“为什么不早点告知我?”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告知您什么?”我看着远处的城市夜景,平静地反问,“告知您林薇抢了我的功劳?证据呢?在结果出来之前,一切都只是我的个人感受。说了,只会显得我像个争功诿过的小人,还会影响整个项目的士气。”
张总沉默了。他知道我说的是实际。在职场里,没有证据的指控,是最无力的呻吟。
“那你今晚……”他欲言又止。
“今晚是最好的时机。”我接过他的话,“她最高兴,最得意,也最没有防备。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只陈述一个实际,剩下的,让实际自己说话。我不想在背后搞小动作,我要把一切都摆在台面上。”
张总又抽了一口烟,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明灭。他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丝欣赏。
“你比我想象的,要沉得住气,也……狠得下心。”
我笑了笑,有些自嘲:“如果连自己亲手种的庄稼都守不住,那我还算什么男人?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而已,谈不上狠心。”
张…总掐灭了烟头,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这件事,公司会给你一个交代。你先回去休憩吧,明天……等通知。”
我向他道了声谢,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却让我感觉无比清醒。我没有胜利的快感,心里反而有些空落落的。为了这片刻的清白,我失去了一个曾经以为的“朋友”,也让自己彻底暴露在了职场的风口浪尖。这值得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今晚我什么都不做,任由她踩着我的肩膀走上高位,那么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在屈辱和不甘中度过。那种内心的煎熬,比目前这一切要痛苦得多。
第二天,我照常来到公司。
办公室里的气氛异常诡异。没有人讨论昨天晚上的事,但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几分敬畏和疏远。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这个敏感的话题。
然后,我看到了林薇空着的工位。
她的东西都还在,电脑,水杯,那盆快要枯萎的多肉,一切都和昨天一样。但她的人,没有来。
上午十点,我接到了人事部门的电话,让我去一趟张总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除了张总,还有人事总监。
张总让我坐下,表情严肃。
“陈阳,公司经过连夜的调查,已经核实了你所说的情况。‘绿洲计划’的核心代码,的确 留有你的个人标记。同时,我们也调取了项目的全部开发日志和版本提交记录,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你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贡献者。”
人事总监接着说:“林薇在项目汇报和晋升材料中,存在严重的履历造假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性质超级恶劣。经过管理层讨论决定,公司已经对她做出了辞退处理,即刻生效。她今天上午回来办了离职手续,已经走了。”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平静。这个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
“另外,”张总看着我,语气缓和下来,“关于你的任命,公司也重新做了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你不仅具备顶尖的技术能力,更具备了正直、有担当的品格。所以,公司决定,任命你为技术部高级经理,即日生效。希望你能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公司创造价值。”
说着,人事总监递给我一份新的人事任命书。
看着上面白纸黑字的任命,我心里五味杂陈。这个我曾经期盼了很久的职位,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到来了。
我没有太多的激动,只是郑重地接了过来,对张总和人事总监说:“谢谢公司的信任,我必定会努力工作。”
走出办公室,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不,目前已经是林薇,或者说,曾经是林薇的那个工位了。她的私人物品已经被行政收拾干净,装在一个纸箱里,放在角落,等着她来取走。
桌上,只剩下那盆无人问津的多肉。
我看着它,想起了三个月前,林薇把它搬来时,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阳哥,我们一起养着它,等项目成功了,它肯定也长得特别好。”
目前,项目成功了,它却快要死了。
我端起自己的水杯,走过去,给那盆多肉,浇了一点水。
第7章 成长与反思
我升职的消息很快在公司传开。
这一次,没有人再涌过来道贺,也没有人起哄让我请客。同事们只是在OA上给我发来公式化的“祝贺”,或者在走廊里遇到时,对我点头微笑,眼神里带着几分客气和距离感。
我清楚,我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开玩笑的老好人陈阳了。那一晚我在庆功宴上的雷霆一击,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隔绝在了“普通同事”的圈子之外。他们或许佩服我的勇气,但同时也对我心存忌惮。
我成了那个“不好惹的人”。
对此,我谈不上喜爱,也谈不上讨厌。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温柔和善良,必须带点锋芒,否则就只能沦为别人向上攀爬的垫脚石。
我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高级经理的职责,远比单纯做技术要复杂。我需要带团队,做项目规划,和各个部门开无穷无尽的会。一开始,我很不适应,尤其是在沟通协调上,磕磕绊绊。
我这才意识到,林薇身上,的确 有我需要学习的地方。抛开人品不谈,她的沟通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向上汇报的技巧,都远在我之上。如果当初我们真的能精诚合作,或许“绿洲计划”能完成得更出色,我们也能成为一对真正的黄金搭档。
可惜,没有如果。
有一天,我在茶水间遇到了之前和林薇关系不错的一个女同事。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来,低声对我说:“陈经理,我前两天……见到林薇了。”
我端着咖啡杯的手顿了一下:“哦?她还好吗?”
“不太好,”女同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在一个小公司的面试上碰到的。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听说我们公司对她的处理结果,在行业圈子里传开了,背调过不了,许多大公司都不敢要她。”
我心里一沉,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她活该,”女同事撇了撇嘴,“但说实话,也挺可惜的。她能力是真不错,就是心术不正,太急了。”
是啊,太急了。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每个人都想走捷径,都想快点成功。林薇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她或许觉得,靠自己的能力慢慢熬,太慢了,所以才选择了那条看起来最快的路,结果却摔得最惨。
我回到办公室,坐在宽大的经理椅上,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陷入了沉思。
这件事,我赢了吗?
从结果上看,是的。我拿回了属于我的职位和荣誉,林薇也为她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但从过程上看,这是一场惨胜。我失去了一个曾经的朋友,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也让自己背上了“心机深沉”的标签。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开始反思自己。在这件事里,我难道说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有。我的责任,在于我前期的“包子性格”。我明明察觉到了不对劲,却由于害怕破坏关系、害怕冲突,而选择了忍让和沉默。我的退让,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她的野心,让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软柿子,最终导致了矛盾的彻底爆发。
如果我能在第一次发现她侵占我的功劳时,就找她开诚布公地谈一次,或者在项目中期,就通过邮件、周报等正式渠道,明确地记录下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贡献,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
职场不是温情脉脉的象牙塔,清晰地界定自己的工作边界,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一种必要的职业素养。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释然了许多。
我不再纠结于过去的是非对错,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未来。我开始学习管理知识,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我努力让我的团队成员,每个人都有清晰的职责分工,每一次的贡献都能被明确地记录和看到。我希望,在我的团队里,不会再有第二个“陈阳”,也不再有第二个“林薇”。
几个月后,我路过楼下的花卉市场,鬼使神差地,又买了一盆多肉。
我把它放在办公室的窗台上,和我从林薇工位上“继承”下来的那一盆并排放在一起。那一盆老的多肉,在我断断续续的浇灌下,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还从干枯的根部长出了新的嫩芽。
两盆多肉,一盆是过去的见证,一盆是未来的开始。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给它们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我看着它们,心里一片宁静。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职场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风浪。但我不再害怕了。由于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坚守内心的那份光明。
这或许,就是“绿洲计划”带给我最重大的,也是唯一的“功劳”。
相关文章